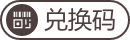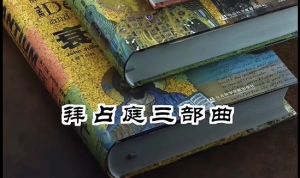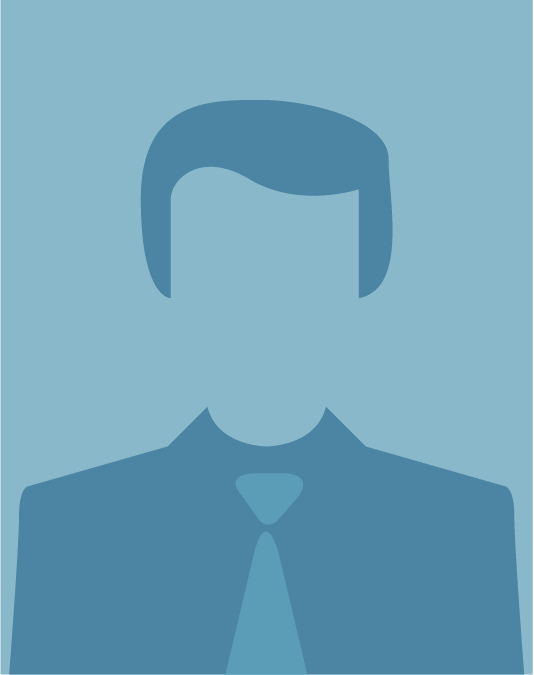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03出版
幽灵帝国拜占庭: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传奇旅程
10分
|3人在看

先晓推荐
刘禹锡有诗云,“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下阙也说,“念往昔、繁华竞逐…….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中国人寻踪访古,最后大多以自然之景慰藉心怀,原因是“故垒”实在少之又少。西方人似乎要幸运一些,在伊斯坦布尔游历时,映入眼帘的是千年前斗兽场的废墟,大理石雕像的残骸,雄伟的大教堂和清真寺,狄奥多西城墙、蓄水池和大赛马场遗址等……手之所触,目之所及,似乎总能嗅到一点儿历史的气息。
建筑材质不同是一说。难道中国人更注重精神,西方人更物质吗?前者明明是“重实践,不喜玄想的民族啊,后者则尚玄想必本诸事实”。从历史教育来看,有“事实”所本毕竟还是好的,要不然,就只有求诸文字这一条途径了,虽说所失不多,但终归不够“鲜活”。乔伊的历史教育或许是典型的西方式,但伊斯坦布尔又是所谓东西方分界处的历史名城,故抚今追昔时,总好像带了些东方情调。
相关海报
视频读书
详情
内容介绍
参考文献
图书详情
ISBN:978-7-5201-4061-4总页码:504
字数: 385千字装帧:精装
内容简介
2014年,理查德·菲德勒带着儿子乔伊完成了一次伊斯坦布尔之旅。着迷于拜占庭帝国光辉灿烂又丰饶复杂的历史,围绕着传奇城市君士坦丁堡,菲德勒在旅途结束之后写下此书。于是,读者得以窥见拜占庭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故事,包括文明的冲撞,帝国的陷落,基督教的兴起,复仇、贪欲和谋杀。随动荡故事同时展开的,则是父子间关系的悄然转化。历史、回忆与感受相互交织,犹如教堂墙壁镶嵌的马赛克图画,异彩纷呈。拜占庭帝国的盛衰,与君士坦丁堡这座大城的沧桑变迁,均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展开
内容资源
目录
卷册
附属资源
图片
图表
音频
视频
请选择图书

0:00
- 1.0
- 1.5
- 2.0
-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