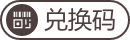章节
“政府造社会”: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生产”实践
摘要
城市社区居民的自组织,一直被看作“社会生产”的可能路径之一。近年来,地方政府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似乎开启了一条以政府他组织的方式促进社会自组织的“社会生产”新路径。本文通过分析“政府造社会”的含义、动力来源、实现渠道和实际效果,指出尽管“生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地方政府在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过程中的 “未预结果”,但客观上为社会的生产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机会和可能性。同时也应看到,国家的外部赋权并不必然促成社会的内部增能,有时反而可能加深社会对国家的依赖、造成社会内部的撕裂,或是强化基层政府的管控。也许,只有通过“完整赋权”,才能使“政府造社会”成为社会生产的更有效路径。
作者
史云桐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城市和政治社会学。
检索正文关键字
章节目录
- 一 “相互对抗”还是“相互增能”:重返国家与社会关系
-
二 “自组织”抑或“他组织”:社会生产的双重路径
- (一)社会生产空间初显及社会生产的双重路径
- (二)“组织困境”与“行动困境”——自组织的社会生产困境
- (三)从“缓慢撤退”到“积极能促”——他组织的社会生产实践
-
三 “政府造社会”的地方实践
- (一)“政府造社会”的动力来源
- (二)“政府造社会”的实现渠道
- (三)“政府造社会”的客观效果
- 1.“独立”抑或“依赖”——制度运行的急促性
- 2.“黏合”抑或“撕裂”——政策运行中的不完整赋权
- 3.“放权”抑或“集权”——科层体系内部的结构张力
- 四 结论和讨论
相关文献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