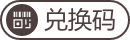-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博物馆旧事:美术馆大劫案的书写
作者:顺手牵猴
来源:《博物馆窜行记》
发布时间 2019-12-20 19:21 浏览量 240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一百年前,很多欧洲废墟的建筑部件,被人整装运到美国,重新拼装成古建筑的样子,有些成了土豪新宅的点缀,有些则被用于建造博物馆。
那一波仿旧潮流中,大都会远非孤例,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也有很多装饰部件来自欧洲。一些柱头和墙饰,取自不同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遗迹,镶嵌在水泥结构中,拼贴出一幅马赛克式的文化图景,就像古代的宗教机构,往往会用来路不明的圣体、圣物、舍利子,彰显身份地位的合法性。加德纳博物馆于1900年动工,于1903年元旦建成开放。揭幕酒会聘请了当时最好的波士顿爱乐乐团演奏助兴。
加德纳博物馆的建筑,并非本地常见的殖民地式样,而是以威尼斯的巴尔巴罗宫做样板。那是大运河上一新一旧的一组宅邸。老的那座,是典型的威尼斯哥特式风格,临水的外墙上带有石雕的立柱和花型窗饰;后来加建的巴洛克式部分,包括一间著名的书斋,里面的天顶壁画,出自最后一代洛可可大师提埃坡罗(Tiepolo)之手,后来成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收藏。
在改编自伊夫林·沃小说的英剧《故园风雨后》中,男主角随贵族朋友到威尼斯探访老爸,就是住在这栋建筑里。剧中,老主人听说年轻人正在学画,问他最想去看哪些名家的作品。
“贝利尼大师。”年轻人回答。
“哪个贝利尼?”又问。
“难道还有两个?”
“三个。”
16世纪,威尼斯的贝利尼一家,以绘画闻名当地,老爸雅各布调教出两个著名的儿子:詹蒂莱和乔凡尼。哥哥原本负责总督府装修,可工程做到一半,因为国际政治需要,被总督遣往伊斯坦布尔,为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画像。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就以这段历史为蓝本。弟弟对于后世艺术影响更大,除自己成为一代宗师,又带出乔尔乔内和提香这样两个名垂青史的徒弟。这段题外话是想说,这种地方的文化家底,外人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走的。
随着“镀金时代”的美国富豪拥入欧洲置产,那座老建筑也被抄底。落入美国人之手后,巴尔巴罗公馆反倒增加不少文艺范儿。亨利·詹姆斯曾在这里写作;法国画家莫奈到威尼斯写生时,也在此落脚;美国画家萨金特则在这里为主人寇蒂斯一家画像。1894年,瑞典画家安德斯·佐恩(Anders Zorn)接受委托,在这里完成了一幅肖像,画中人物正是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
这位女士原本是纽约一个成功实业家的千金,早年就学巴黎时,养成了奢侈的艺术口味。而她的夫婿约翰·加德纳则是波士顿人,家世人品也是一时之选,后来成了航运业巨头。独子夭折后,这对夫妇经常回到欧洲旅行,搜购古玩和艺术品,而威尼斯则是他们的最爱。然而约翰也未享天年。
寡居的加德纳夫人回到波士顿,抚育几个养子之余,所有心血都花在创建一座博物馆,用来展示她和亡夫多年积累的艺术收藏,也为自己多年旅居威尼斯的记忆最终选好一处下碇之所。然而波士顿虽有查尔斯河经过,却不是水巷纵横,所以建筑更多着眼内部,而不是外观。遇到一个情怀值爆表的甲方,设计师基本沦为土木工程师,只需把雇主的各种念头一石一瓦搭建出来,然后拿钱走人。
建筑的核心是一座玻璃棚顶下的室内花园,环顾四壁,里面才是巴尔巴罗公馆外墙的样式,好像把摹本建筑里外翻了个个儿,只是没有运河。展品布置方面,这里更像欧洲旧时代富贵人家的私人空间——家具、壁饰、地面,都是威尼斯的老款式——但是和现代博物馆大异其趣。
这里,观众可以看到一个年轻、文化上幼稚的美国。它的上层阶级奋力跻身文明世界,热切地期待文明中心的认可,虽然他们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经济体量,虽然他们的欧洲表亲更多会对充满南方土风的爵士乐,或是“水牛比尔”代表的蛮荒西部表现出屈尊俯就的热情。
新兴大国面对精致文明,总有羞于启齿的自卑和向往。对高端事物略知一二的外省精英,面对势利刻薄的文明人,不时报以鄙夷。那里,除了教堂、剧院和博物馆,其他所有的大门,并不对他们敞开。还有一种人比较强悍,比如加德纳夫人。这类人试图移植欧洲的全部记忆和想象:从园艺、饮宴、室内乐、沙龙谈话到艺术鉴赏。但那只是一个经过编辑的想象的欧洲,去粗取精后,只剩下文化经典。经典记录的,是人类行为和心理中变化最少的部分,同时经典也在规约人的行为和心理。其副产品是重复,也就是俗套。所谓俗套本意是“雅套”,只是一切风雅,落套便俗。这是审美上的kitsch。这个词曾被装模作样地译作“媚俗”,或是其他,基本都属于扯淡。人之所媚,其实是雅,只是他们把主题的永恒,误会成风格的无限次回收。
美国精英也曾追捧经典。那个时代不时兴祛魅,大家还都端着,而且是真心诚意地端着。好在他们没去复制曾经产生那种经典的等级社会。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鼓励创新的美国,而不是等而下之的欧洲复制品,虽说美国的消费文化也会容忍甚至鼓励迪士尼式的正能量“鸡屎”风格。咱们还是音译吧,就像英特尔(intel)或者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
加德纳美术馆拥有世界级收藏。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波提切利的《卢克蕾希亚之死》。作者的名头先不算,单说五个世纪前的蛋彩画,能有多少保存至今?画中的故事来自古罗马,女主角是历史上有名的烈女。当时罗马还是王政时代,国王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靠发动叛乱篡得王位,并图谋把元老院推选君主的传统改成世袭制。由于种种不义之举,这位僭主留下“傲慢者”(Superbus)的绰号。一次对外战争期间,他的儿子强奸了一位执政官之妻卢克蕾希亚,结果引起复仇兵变,国王家族被驱逐,罗马进入共和时代。另一件文艺复兴名作出自威尼斯大师提香之手。这幅取材希腊神话的《劫夺欧罗巴》,描绘的是克里特岛上的欧罗巴,被化身公牛的天神宙斯劫拐到北方的大陆。这也是欧洲命名的起源。
名家作品不止于此。威尼斯另一大师丁托列托的《黑衣女》,以及伦勃朗早期的一幅自画像,也都是精品。这里还能看到意大利的乔托(Giotto)、拉斐尔、乌切洛(Uccello)、贝利尼父子、布伦齐诺(Bronzino),尼德兰的凡·艾克(Van Eyck)、鲁本斯,德国的丢勒和西班牙的苏巴朗(Francisco de Zurbaran)、委拉斯凯兹等的作品。你还能看到法国的布歇(Boucher)、马奈、德加(Edgar Degas)、马蒂斯,还有出身美国的惠斯勒(Whistler)的创作。
别忘了加德纳夫人的朋友萨金特。他的贡献是早年在巴黎沙龙的成名作《西班牙舞者》,从笔法到设色,处处表现出青年萨金特游历西班牙、刻苦研习委拉斯凯兹的心得。它也是这位美国画家媒体曝光率最高的作品之一,或许仅次于现藏于大都会的《X夫人》。对于有些人,这些展品正齐声呼唤:偷我吧!
1990年3月18日。那是个雨夜,爱尔兰裔居民众多的波士顿,刚刚过完圣帕特里克节。两个穿警服的男人,把车停在位于芬威区的加德纳博物馆外。他们下车后按了门铃,自称这一带有人闹事,被上面派来调查。门卫违反夜间值班规定,开门放进了这两个外人。这个警卫名叫里克·阿巴斯,是个摇滚青年。那天在当班之前,他刚和乐队一起参加过一场演出。从技术上说,起身开门也是一个严重失误,意味着一旦有事,他根本来不及返回原位按警报电钮。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如同警匪片。
两个假警察进门后,检查了阿巴斯的证件,命令他面朝墙站,然后把他从背后铐了起来。另外一个警卫正在四处巡视,听见动静后从楼上赶到前台,但也被迅速制服。他们告诉两个倒霉蛋:“这是打劫,先生们!”进入展区后,劫匪直奔荷兰厅,先对那幅伦勃朗的自画像下手,却触发了警报装置。慌乱之中,他们随便顺了几件东西,然后窜到其他展厅。
一夜之间,博物馆损失了13件藏品,包括中国商代的一座铜觚,估价总值约5亿美元。由于馆内装有动作探测器,作案过程被记录下来。不过,此案至今未破。失窃后的加德纳博物馆,人气反倒更旺。大批观众流连于空画框前,默悼一段失去的记忆。那些空画框至今仍悬挂在展厅原来的位置,像是证明记忆的空洞也是记忆的一部分。
在被盗藏品中,约翰内斯·维米尔的名作《演奏会》画幅较小(72.5厘米×64.7厘米),估值最高,超过2亿美元,而且有价无市。毕竟这位代尔夫特大师的作品,现存不过三十余幅。画中,一个姑娘坐在羽管键琴前,跟一个弹鲁特琴的男人合作,为一个拿着歌篇视唱的女人伴奏。这是17世纪“黄金时代”荷兰富裕市民的典型日常生活景象。伦勃朗的《加利利海上的风暴》,表现《圣经·新约》中耶稣基督的一次神迹。此外,马奈的《在托托尼》,则是法国印象派时期的杰作。
为追回失窃藏品,博物馆开出500万美元赏金,引得一批歹人浮出水面,一时众声哗然。有人透露赃物已被运到爱尔兰,也有人说去了以色列,还有人说东西落到一个同性恋神父手上。除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执法机构,也有一些私人侦探甚至调查记者介入此案,但所有线索最终都引向死端。
首先罪犯的作案动机就是个谜,加之线报大多来自市井小贼,连维纳斯和米老鼠都分不清楚。也许幕后主使的趣味独特,在窃贼锁定的目标当中,包括5幅德加的素描,而价值远高于此的米开朗基罗、提香和拉斐尔的作品却得以幸免。考虑到这一类贼赃极为烫手,几乎没有变现的可能——偷画不像偷车,每一件涉案作品都是流传有序的海内孤本,极易追踪——罪犯的动机基本无以揣度。这也是此案难破的原因之一。
当年的安保措施形同儿戏,根本无须电影《纵横四海》中的手段。长达81分钟的作案过程,虽然一度被警报打断,可入侵者却能继续从容作业,而且撤离之前,还有时间毁掉监控设备中的录像资料。引狼入室的警卫阿巴斯后来回忆说,他被铐在配电箱上,为了给自己壮胆,一直在唱鲍勃·迪伦的《我最终会被释放》(I Shall Be Released)。然而,2015年波士顿警方公布了案发前一天夜里的一段监控录像,从中可以看到,这个警卫也曾开门放进一个陌生人,此人用竖起的衣领遮住了五官。
阿巴斯从未向查案人员提起此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段录像何以等到20多年后才浮出水面?至于博物馆为什么不找靠谱的专业警卫,非要雇用一个经常嗑药的嬉皮,据说那是董事会不懂事,盲目削减预算的结果。执法当局曾锁定两名嫌疑犯,但从未公布他们的身份。这两个人,一个已经死于癌症,另一个则在与黑帮火并中丧命。2016年初又传消息,一个因为其他罪名而在押的嫌疑犯可能涉入此案,而且突然获得减刑。有人猜测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
虽说事过多年,但这桩旧案并没有冷透。就在不久前,旧金山一位日裔德国籍画家,又把当年失窃的13幅画作重新画了一遍。当然,这些新作的风格技法,与原作都有相当的距离——实现拟真仿作,恐怕得靠人工智能——只能算是一种纪念性的姿态。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究竟谁能拿到那500万美元赏金?
作为一桩世纪大案,涉案赃物如此惹眼,除非是想据为禁脔,否则很难保证贼人不会销赃灭迹,以防引火上身。
©️本文版权归作者【先晓书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