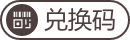-
分享
- 评论(1)
- 点赞(0)
- 收藏(0)
三种北京记忆与三个时代
作者:张慧瑜
来源:城市北京与文化书写——北京题材影视剧研究(1978-2018)
发布时间 2020-04-21 00:02 浏览量 2121
-
分享
- 评论(1)
- 点赞(0)
- 收藏(0)
旅客朋友们,列车前方将要到达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历史古城、文化名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金元明清等数代王朝曾在这里建都。有着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850余年的建都史的北京,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早在7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群落“北京人”,北京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
从北京高空俯瞰,规模宏大的帝王宫殿、园林、庙坛、陵墓及其他古代建筑井然有序、错落有致,俨然可见昔日皇城的威严。北京的宫殿建筑首推故宫,它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大的宫殿,原为明、清两代的皇宫,其建筑具有典型的中国古典风格,是我国最珍贵的文化和艺术宝库之一;故宫前面的天安门广场能容纳100万人在此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之一,建筑雄伟,气魄非凡,被称为“中国的心脏”;颐和园兼有江南水乡的玲珑精致和北方园林的豪迈大气,园中山青水绿,景色宜人,在中外园林史上享有盛誉;天坛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也是世界建筑艺术的宝贵遗产,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和“祈谷”的地方,布局完整,环境优美;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北京境内诸多长城关隘形态各异,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历尽沧桑雄健依旧;北京的宗教建筑同样多姿多彩,有佛教圣地碧云寺、道教圣地白云观、喇嘛教圣地雍和宫、伊斯兰教的牛街清真寺、基督教的西什库教堂等;明十三陵是北京最大的古墓群,内有明代13个黄帝的陵墓,尤其以长陵规模最为浩大。
此外,北京作为我国的文化中心,除拥有许多文化遗产如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和众多的名人故居,还有现代科技的结晶——中关村。许多著名的学府如清华、北大等也汇聚于此。您尽可以漫步校园中想象朱自清、胡适等昔日大师在校任教时的情景。
北京周边山青水碧,优美的自然景观同样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每一位乘火车来北京的人们来说,听到这段火车上的广播语,意味着北京就要到了。从1998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来读大学,以后每年都要在北京与山东老家之间往返数次,这段广播语也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初到北京,我最先去的地方就是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等耳熟能详的名胜古迹。广播语用客观平实的语言叙述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北京,尽管伟大的首都、“中国的心脏”、天安门更联系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的意义,但整体上给人们的感觉这更像是一个古老的老北京。这种老北京也确实是19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中所塑造的北京主体形象,包括城南文化、胡同文化、四合院等文化符号。
记得在上大学期间的某个暑假,我偶然看到姜文导演1994年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开头主人公带着无限回忆的口吻说:“北京变得这么快,二十年的工夫她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就是这样一部“分不清幻觉和真实”的青春片不仅讲述了一个与1980年代城南北京、民国北京不同的北京故事,而且把1980年代所塑造的伤痕、负面的革命年代借青春的外衣书写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来,我知道姜文电影背后是王朔1980年代中期后所创造的北京顽主的形象,这是一种以北京军队大院为空间依据的文化想象。从这种成长于部队大院的北京记忆可以看到1950年代到1970年代单位制下的北京。这种带有青春怀旧色彩的北京故事一方面拉开了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中对于革命年代、革命岁月的正面书写;另一方面也成功、有效地把与革命有关的记忆与消费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结合起来。
在北京学习、工作的十余年间,我还遭遇到一个更加现实的新北京,这就是迅速发展的、处在高速变化之中的现代化北京。记得1990年代末期中关村附近的四环路刚刚竣工,2006年我已经在五环外的肖家河定居。从1990年代末期到现在,北京像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最直观的印象就是随处可见的建筑工地和一片又一片崭新的楼房。印象中2008年奥运会前后几年是北京城市空间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城市地铁四通八达,四号线也修到了我所在的西北五环之外。更不用说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还有东三环外高楼林立的CBD商务区,这些都成为新的北京地标。与这种新北京最相关的作品是2007年以《奋斗》为代表的青春职场剧的热播和2011年以《失恋33天》为源头的青春片的热映。这个后工业化的新北京成为都市白领、中产阶层讲述职场竞争、爱情生活的大舞台。只是这种职场爱情的励志剧很快转化为钩心斗角的腹黑剧,青春、小资也蜕变为渴望逆袭的屌丝和机关算尽的腹黑女。
从这种火车广播语中所描述的古老北京,到姜文借王朔作品所呈现的大院文化,再到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日新月异的新北京。可以说,这样三种北京记忆就是笔者研究1980年代以来北京都市文化形象的起点和基本坐标。
笔者把“城市文化符号生产与北京题材影视创作”的演变分成三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1980年代,大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转型到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依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二是1990年代,从小平南方谈话到2001年加入WTO,中国处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双轨制”阶段。三是21世纪以来,市场化成为主导性的力量,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直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过,经济崛起之后,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这样三个时代就像历史的台阶,有拾级而上(下)的延续性和相仿的主旋律,如现代化、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等,又有各自平台上截然不同的主题,这三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框架。下面我仅选三个作家,把其放在三个时代背景中来探究时代变迁的层级和文化想象的界限。
这三个作家分别是王朔、王小波和郭敬明,他们对应着新时期以来的1980年代、19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把这样三个作家放置在一起看似有些奇怪,因为他们的文学风格各异,也没有任何师承关系,但他们却是每一个历史台阶中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作家,他们之间的断裂和差异就像这样三个异彩纷呈的时代一样。如果说王朔是1980年代少有的不依靠作协制度和文学思潮在文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那么王小波则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成为1990年代的文化英雄,而郭敬明更进一步,不仅是文学市场最大的宠儿,而且也是打造青春文学市场的出版人。尽管三个作家一开始不被主流文学秩序所接受,但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各自时代最受市场这一新体制欢迎的作家,这也说明他们的创作以及人们对于他们的接受高度应和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需求。他们不仅是与三个时代最为合拍的作家,而且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核心命题,这正是他们作为时代标识的意义所在。
相对19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秩序,他们显得有些边缘和游离。王朔并不被放在1980年代主要的文学思潮中,他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都不一样,反而在1990年代城市文学视野中被作为京味文学的传承人。与城南、胡同、天桥艺人所勾画的老北京图景不同,王朔以军队大院子弟的身份彰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进城解放军对红色北京的文化记忆。作为1980年代最早下海的作家,1988年有四部作品同时改编为电影,该年也被称为“王朔电影年”,1992年《王朔文集》出版并热卖,成为“文革”后首次版税付酬制的作家。王小波也是如此,他的创作很难划到1990年代以来新写实、新历史、断裂作家等纯文学序列中,其“时代三部曲”既有表现“文革”的知青故事(《黄金时代》),也有书写未来故事(《白银时代》)和“故事新编”式的唐代传奇(《青铜时代》),作品多处理为后现代的戏谑和个人命运荒诞等存在主义主题。除了小说家的身份,王小波凭借自由撰稿人的角色被当作1990年代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代表。
与王朔、王小波通过文学期刊或获奖来引起关注不同,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作家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这是由《萌芽》杂志针对高中语文教育应试化而面向中学生举办的“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作文大赛,就像“超男快女”的音乐选秀一样,大赛发掘了一批“80后”青少年作家。这种更加市场化的文学生产方式改变了作家依靠文学体制(各级作协及文学期刊)成名的模式,因此,韩寒、郭敬明从一开始就是体制外的离经叛道者。相比高中退学成为职业赛车手的韩寒对文坛以及社会现象保持着王小波式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同样在上海发展的郭敬明则深谙文学市场的秘密。在连续获得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之后,郭敬明于2002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爱与痛的边缘》,2003年出版的玄幻小说《幻城》销量过百万,获得更高知名度。此时,郭敬明看到了文学市场的潜质,开始与出版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成立工作室、文化传播公司,不光出版自己的作品,还策划、编辑文学杂志,发掘、包装新作家,就像《小时代》中集时尚与资本于一体的杂志帝国《M.E》一样,郭敬明已经成为占领“上海滩”的文化传媒大亨。自2006年设立中国作家富豪榜以来郭敬明多次排名首位并始终名列前茅,在其“青春不老”的面庞下面有一颗成熟老练的心灵。
先看王朔与1980年代的关系。王朔登上文坛是1984年在《当代》杂志发表处女作《空中小姐》,直到1992年发表《你不是一个俗人》《过把瘾就死》等小说,此后王朔更多地投身于影视剧制作,虽然也发表文学作品,但其文学成就和风格基本集中在1980年代中后期,这也正是王朔的1980年代。王朔所创作的最经典的文学形象,就是喋喋不休和扬扬得意的“顽主”。其喋喋不休是为了嘲讽、解构一套又一套的“正统话语”,把庄严、正襟危坐的正统叙事变成假正经和蝇营狗苟,与此同时,顽主又是扬扬得意的精神贵族,这来自其纯正的革命之子的身份(“文革”后期成长的比红卫兵、造反派更为年轻的红小兵),这些人自认为有藐视知识分子、社会权贵的资本。顽主的这样两重面向被1990年代王朔的两位精神传人冯小刚和姜文发扬光大,前者是葛优所扮演的浑不吝、油嘴滑舌的北京痞子,后者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戏仿父辈革命事业的青春男孩以及《让子弹飞》中带领弟兄智斗土豪的孤胆英雄。这就使得顽主一方面是“一点正经没有”的玩世不恭者;另一方面又是不甘流俗、平庸的青春不羁者。
顽主之所以能够出现,与1980年代备受诟病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也就是说顽主对于正统叙事的嬉笑怒骂,在于1980年代人们(尤其是城市居民)依然生活在顽主所不屑的社会单位制之中。就像1990年代初期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满口正统话语的老爷子,虽然被嘲弄,但依然在家中有权威,不过是退休而已。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刚起步。比如国企工厂改革也多采用承包制、奖金制等方式,这与1990年代让大部分国企破产重组不同。就连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也是一种在地现代化的思路,这种“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化路线,使得“在希望的田野上”不是怀念远方的故乡,而是把脚下的故乡变成“四个现代化”的乐土,这与1990年代走向对外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路径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这里,尽管被顽主所解构的正统叙事变成空洞的话语,但是公有制、集体制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这就使得顽主们喋喋不休并非无的放矢。19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大,顽主也就丧失了其言说的社会基础。在这种背景下,王小波式的体制外英雄登上了1990年代的文化舞台。
王小波的创作始于1989年,被人们知晓是1991年《黄金时代》获第13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然后大陆开始出版其作品。王小波真正产生巨大影响则是1997年意外英年早逝,直到2002年逝世五周年,各大媒体对王小波的悼念达到高潮。王小波不仅构造了独特的文学世界,而且在1990年代中期成为给《三联生活周刊》等刚刚创刊的都市文化杂志写稿的专栏作家,结集出版过影响巨大的《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等杂文集。如果说王朔的文学形象是顽主,王小波则书写了一个体制外的“特立独行的猪”,连同王小波本人也被媒体塑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尤其去世后,媒体最经常称呼王小波的是体制外的自由主义分子、民间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这些命名方式是1990年代最为核心的文化想象,即体制内与体制外、官方与民间、体制与独立,还有地上与地下,比如把第六代导演的体制外制作(借助民营资本,而不是国营电影制片厂)指认为独立制片以及没有厂标的地下电影。与此相关的思想社会议题,就是1990年代中后期借助海外汉学以及哈贝马斯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而展开的对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争论。
这种对两种体制和社会空间的想象是1980年代不曾出现、21世纪以来也很少使用的话语言说方式。也就是说,这是1990年代特有的双重体制,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这与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后所开启的市场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1980年代以来,人们把计划经济指认为一种“旧体制”,一种落后的、没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和单位制,而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一边格式化旧体制、一边开始确立市场经济的新体制。王小波笔下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真实含义就是要勇于打破大锅饭、离开旧体制到市场经济中做一只自由、独立的小猪,这些在1990年代反复使用的民间、自由、独立、体制外等话语方式是对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高度认可。这种离开旧体制的自由形象成为21世纪之交在都市消费文化中浮现出来的小资主体的理想镜像,不过,在这幅主动从旧体制走向新制度的图画中遮蔽或消隐不见的1990年代被动走向市场的两类群体,一类是离开土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另一类是国企工厂“强制”破产后的下岗工人,他们虽然也过着市场化的、体制外的“独立”生活,但显然不是“特立独行的猪”、不是体制外的自由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说1980年代的顽主依然生活在社会主义旧体制的松动之中,那么1990年代“特立独行的猪”则成为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弄潮儿。1990年代的两种体制,来自1980年代对计划体制的自我批判。
最后是郭敬明与21世纪以来中国的关系。2013年郭敬明把自己的作品《小时代》搬上大银幕,引发激烈争议,也掀起对大时代和小时代的讨论。《小时代》发表于2007年,2008年以来已经出版了三部曲,是郭敬明近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非常敏锐地把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的时代命名为“小时代”——一个大历史、大政治终结的时代。1980年代以来那种个人与时代命运相连的“大时代”已经逐渐成为过去,不管是1980年代的人性论、“大写的人”,还是1990年代的“特立独行的猪”,都把个人、个人主义放置在社会文化舞台的中心,这与市场经济中个人作为理性人、自由人的主体想象是一致的。而《小时代》的意义在于呈现了21世纪以来个人从“我的地盘我做主”变成了一种“微茫的存在”。在小说开头段落,郭敬明这样描述“小时代”所处的空间载体——上海,“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人们的心脏被挖出一个又一个洞,然后再被埋进滴答滴答的炸弹。财富迅速地两极分化,活生生把人的灵魂撕成了两半。我们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窝里,我们微茫得几乎什么都不是”。《小时代》被描述为一种悖论的状态,几个年轻人(富二代及其朋友)一方面把上海浦东陆家嘴变成他们的“儿童主题公园”,他们在这个中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地带如履平地、一马平川;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甚至是“最最渺小微茫的一个部分”。
与这种“小小星辰”相对应的就是《小时代》关于社会的想象。在小说和电影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是青春靓丽的作家周崇光的致辞:“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突然改变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你被失望拖进深渊,你被疾病拉进坟墓,你被挫折践踏得体无完肤,你被嘲笑、被讽刺、被讨厌、被怨恨、被放弃。但是我们却总在内心里保留着不甘放弃跳动的心。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的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辰。”这段话使用了《小时代》中经常出现的把社会、时代描述为“浩瀚的宇宙”的修辞方式。这种个人之“小”与宇宙、社会之“大”的强烈对比不仅是郭敬明式的“长不大”的少年情结,更是一种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想象。社会中的个人变成了“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也就是说,“我”(个人)被淹没在一望无垠、无边无际的宇宙沙漠里。
这种支配性的、如同如来佛手掌心般的空间秩序,恰好就是21世纪以来中国在从1990年代以对外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向以房地产为中介的金融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确定,对于21世纪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再有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别,也没有官方与民间的对抗,地上与地下的界限也失效了,正如第六代、地下电影所采取的体制外制片方式在21世纪以来对民营资本放开的电影产业化改革中完全合法。借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中国变成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双重体制演变成了单一的社会制度和空间秩序。
这样三个时代与社会主题,从北京题材的影视创作中也能找到印证,是理解1980年代以来与北京有关的城市电影的基础。1980年代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核心命题是离开计划经济体制、为商品化的时代确立新的人格;1990年代到21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帝王剧”和“商战剧”则是成功者、个人主义英雄的故事,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大量平民故事,这延续了北京的传统;2005年以来的青春剧、青春片则分享“小时代”的情感结构,在“无边黑暗”中1980年代大写的人变成了钩心斗角的腹黑者,就连充满理想和气场的《老炮儿》也在“三环十二少”的新北京败下阵来,如同囚禁在笼中的外来生物——一只渴望自由的大鸵鸟。
©️本文版权归作者【先晓书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分享
- 评论(1)
- 点赞(0)
- 收藏(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