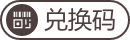-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书摘】chemistry的中文名“化学”从何而来?
作者:[日]沈国威
来源:《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
发布时间 2020-12-29 09:23 浏览量 861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关于译名“化学”的成立,迄今为止科学史研究领域曾有过多次考察,并得出了“化学”系中国制的译词,于幕府末年(1850~1860)传入日本的结论。但是,在近代词汇史研究中(无论中日),还没有专门讨论“化学”得以成立、普及、定型的文章。本章以已有的科学史研究成果为出发点,将译词“化学”放在以上海墨海书馆、《六合丛谈》为舞台展开的19世纪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从译词创制、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角度,对译名“化学”诞生的历程加以梳理。
对于外来的文物,使用汉字进行命名,常常会给该文物的接受、普及带来重大的影响,“化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于“化学”一词的词汇史描述,将对汉字文化圈近代汉字学术用语的产生、交流及汉字文化圈域内共享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这也是本章选择“化学”加以考察的原因。
一 中国的“化学”
关于16世纪末来华耶稣会士们是否带来了西方近代的化学知识这一问题,化学史家袁翰青曾指出:
曾经有些历史学家这样说,近代的科学是在明朝末年传来我国的。就天文、数学等等来说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就化学来说,就不是那样了。……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以及十八世纪前期,化学可还没有建立成为一门近代科学。所以近代化学的传入我国,不可能归之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士。
耶稣会士在他们的著述中介绍了四元素学说,以及阿拉伯的金属、水银、硫黄学说等近代之前的化学知识,但是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远不如天文学、数学那样强烈。当时在欧洲,chemistry也还没有成为学科的名称,所以也不存在将其译成中文的问题。近代化学知识的传来尚须等待新教传教士的东来。
19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们,通过实践认识到,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必须破除人们的迷信观念。为此他们计划出版一批有关世界地理、历史和其他自然科学的通俗读物。但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拟议中的科学启蒙图书实际出版的只有伦敦会传教医生合信的《全体新论》等极少的几种。合信的《全体新论》是把欧洲17世纪以后的近代解剖学、生理学知识介绍给中国的第一本书,在当时受到极大的欢迎。但是该书里没有关于化学的记述。另一本作为英语教材编写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包含了丰富的科学常识的内容,然而关于化学,只有第166课“物质可以细分”,该书里也没有使用“化学”一词。这一时期的著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合信在广州完成,并先后在广州和上海出版的《博物新编》。该书里尽管没有使用“化学”或类似的词语,但是介绍了“养气”“淡气”“轻气”“炭气”等的性质和制造方法,还涉及了“磺强水”“硝强水”等无机酸类。日本化学史家岛尾永康指出:
在此之前明清两代的关于强水的记述,都没有涉及其种类。《博物新编》首次提示了“硝强水”(或称火硝油,现称硝酸)、“磺强水”(或称火黄油,现称硫酸)、“盐强水”(现称盐酸)等无机酸的命名法。“硝强水”“磺强水”“盐强水”等名称还为1870年以后的化学译籍所采用。
袁翰青则指出:磺强水等是广东一带的名称,外国商人等为了自用或商用带进中国后,和外国人交往的中国商人、水手、仆人等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化学物质。而关于这些化学物质的命名,袁翰青进一步说: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工人和商人开始认识一些化学物质并且替它们取了中文名称……为什么这样推测呢?我们可以从早期的译名上看出一点线索。明末清初传教士的科学译名是靠知识分子帮助的,所以一般译名都“文雅”,如像“天步”“坤舆”“格致”等等。至于初期的化学译名却相当通俗,如像磺强水、硝强水、盐强水以及养气(或生气)之类,都不像是知识分子想出来的。这些名词极可能是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
如果袁翰青所说的“群众”是“非专门家”意思的话,那么,“化学”的命名与此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与一般民众无涉的19世纪中叶外语辞典中的情况。
Chemist 丹家(马礼逊:《英华字典》,1822)
Chemist 丹家(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1844)
Chemist 烧炼的,炼用的,炼药的,丹家,制炼家(麦都思:《英华字典》,1847~1848)
Chemistry 丹灶之事,炼用法(麦都思:《英华字典》,1847~1848)
马礼逊和卫三畏的辞典没有收录chemistry,而chemist则被译作“丹家”,西方的化学被与中国道教的炼丹术联系在一起。可以推断,辞典的编纂者对近代化学并没有较多的知识。而麦都思的辞典,尽管收录了chemistry,但同样是从炼丹术的角度来解释词义的。译词中“炼”字是麦都思独特的译法,应该给予注意。在这些辞典之后,同样在广东编纂的辞典还有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该辞典的情况如下:
Chemica,pertaining to chemistry 炼法的,炼的,制炼的,物质理的
Chemist,a person versed in chemistry 炼法者,炼物者,炼法师,制炼法者
Chemistry被用于语义的解释,但是没有单独作为词条列出来。像《英华字典》这样的大部头辞典,不收chemistry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与麦都思的辞典相比,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从译词中删去了“丹家,丹灶之事”,而“炼”字则成为所有译词的构成语素。从“物质理的”这一新译法中可以看出,罗存德似乎想以此来表达自己对chemistry独特的理解。其实,罗存德在这部辞典中显示了对化学的特殊关心。关于罗存德对化学元素的命名,我们在本书“新词创造编”第二章中已经做了专门的讨论,此不赘述。这与其说反映了罗氏的化学观,毋宁说是他对不同文化的接触、融合所持的基本态度,这与罗氏在中国布道的立场也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罗存德过多地迁就了中国的传统。关于罗氏的化学观,我们将在下面再讨论。
日本学者坂出祥伸最先指出“化学”一词首见于上海出版的综合杂志《六合丛谈》。坂出从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藏的和刻版《官版六合丛谈删定本》中检出三处五例“化学”。此后,日本的学术界一般将《六合丛谈》上的例子认作“化学”一词的首见书证。
而在中国,直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化学”一词的来龙去脉还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1981年,潘吉星发表论文《谈“化学”一词在中国和日本的由来》。这是第一篇涉及“化学”词源以及该词在中日间交流的汉语论文。潘吉星根据日本的研究成果,指出《六合丛谈》使用了“化学”,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新发现:《格物探原》(韦廉臣)卷三第一章第一页中有“化学”的使用例。潘氏使用的是《格物探原》1880年的刊本,但认定该书刊于1856年。据此,潘吉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化学”一词《格物探原》首出,《六合丛谈》亦见,并被冯桂芬用于《校邠庐抗议》(1861年成书),其后在中国普及,同时传入日本。与潘吉星的论文时间相同,袁翰青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此后,潘吉星又于1984年写了一篇英语论文“Some New Materials about the Early Use of the Words化学and植物”,投给日本的《科学史研究》,并于第二年译成日语刊登在该杂志上。这篇论文的内容和前一篇大致相同,只是对《格物探原》的刊年有了进一步讨论。因为在前稿中,潘氏对《格物探原》刊年没有进行论证。关于这一点袁翰青的论文也是一样。潘吉星在后一篇论文中说,《格物探原》初版虽然没有标明刊年,但是,韦廉臣投给《六合丛谈》的《真道实证》内容与《格物探原》完全相同,可以认为后者是前者的改订增补版。尽管韦廉臣在《真道实证》中没有使用“化学”一词,但是,他在1857年底回英国养病之前,完成了《格物探原》,并付诸出版。该书最迟于1858年问世。潘吉星似乎认为《真道实证》在增补改订为《格物探原》时加入了“化学”。对于韦廉臣于1857年或1858年完成《格物探原》的说法,潘吉星仍然没有给出证据。但他是第一个把《格物探原》和《真道实证》联系到一起的学者。然而,《真道实证》和《格物探原》并不像潘吉星所说的那样内容完全一样,不能简单地看作增补改订的关系。《真道实证》是在《六合丛谈》第二号至第十一号上连载的传教文章(第六号未刊登),每一期有类似于“上帝必有”“上帝非太极”等的宗教性小标题。在第二号的“上帝必有”和第五号的“上帝惟一不能有二”中,著者分别介绍了化学和动物学的知识。而《格物探原》的刊行不是在1857年或1858年,而是在1876年。该书的初版就已经是三卷一百八十一张对开页的大部头了。《六合丛谈》卷一第二号“真道实证 上帝必有”的化学部分被编入《格物探原》首卷“论物质”第一章中,但是《真道实证》的四页四行以下被删除。该部分是关于水、硫黄酸、钙化合物合成的说明。在《格物探原》中使用了“化学”的是《真道实证》中所没有的“论元质”第一章,韦廉臣在这里把原子译成“微渺”。他在举例说明了原子的“配合”之后,做了如下的总结性说明:
读化学一书,可悉其事,故此微渺,有类于砖石,能建屋宇。
所谓的“化学一书”显然不是指外文原著,而是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处出版的数种冠以“化学”书名的中文译著之类(详后)。其证据是《真道实证》中的金属性元素并没有都加上金字旁,而《格物探原》的元素名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化学鉴原》一致,使用了新造的带金字旁的字。
就“化学”的首例书证提出新见解的是台湾大学化学系教授刘广定。刘广定指出:汉语的“化学”一词是1854年由李善兰与英人艾约瑟创制,并用于两人合译的《重学》第十九卷中;《重学》一书译稿完成于1854年,但是刊行一再拖延,所以最先公开使用“化学”的是《六合丛谈》。
其后,刘广定在王韬咸丰五年二月十四日(1855年3月31日)的日记中找到了更早使用“化学”的例子。这一发现使刘广定于1992年再次发表论文《中文“化学”源起再考》,对前论文的结论做了如下的修正:1854年译完的《重学》仅十七卷,行世的二十卷本,包括使用了“化学”的卷十九在内的后三卷的完成时期无法确定。但是,根据王韬日记中的例子,“‘化学’一词最晚乃在清文宗咸丰四年(1854)由上海墨海书馆中之华洋学者所制定,不一定只是李善兰与艾约瑟两人”。刘广定发现的王韬日记中的例子,是现在我们能确认的最早的“化学”用例。
另外,丁韪良在其《格物入门》的重订增补版卷头序言中说:
至化学一卷,当是编之初创也,中国唯有丹家之论,尚无化学之名,其名创于是编,流传至今。(《重增格物入门·自序》,1900)
“初创”云云并非事实,但是关于“化学”一词早期的使用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未完待续……)
©️本文版权归作者【先晓书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