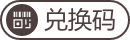-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中国古代东北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丨第一章 第二节 鲜卑的体育文化
作者:隋东旭
来源:《中国古代东北民族体育文化研究》
发布时间 2021-05-25 10:53 浏览量 209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第二节 鲜卑的体育文化
鲜卑是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鲜卑之名,在文献中最早见于《楚辞》与《国语》。按《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又按《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云:“鲜卑,东夷国。”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鲜卑应该就已经存在了,是东夷民族的分支。早期的鲜卑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自战国以降,至汉末时期檀石槐建立鲜卑部落联盟,鲜卑一直以松散的游牧部落形态存在着,他们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都与游牧活动密不可分,随着鲜卑与中原地区汉族的不断深入接触,汉文化开始影响并逐渐改造着鲜卑的民族文化。到了北魏时期,由于鲜卑的南迁与魏文帝汉化政策的全面施行,鲜卑与汉民族逐渐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在这种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转型的过程中,鲜卑民族的体育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一 鲜卑的骑射狩猎体育文化
鲜卑民族的生产群居方式及其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决定了早期的鲜卑体育活动“主要表现为游牧经济下的狩猎骑射”。汉初时,鲜卑“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其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并不多,因此关于早期鲜卑社会发展情况的记载在文献中保存得较少,一直到东汉时期才开始逐渐丰富,而在这些文献中,关于鲜卑早期体育文化发展状况的记载也并无直接描绘,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其他资料对之进行间接的考察。
早期鲜卑的民族体育内容,最为主要的表现就是以骑射为中心的体育活动。按《三国志》引《魏书》:“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这说明汉代时期的乌桓与鲜卑在习俗乃至社会日常生活中是十分相似的。按《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乌桓》记载,汉代的乌桓:“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鲜卑与乌桓一样,都是游牧民族,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使骑射成为他们不得不精通的全民性的生产与生活技能。
从史料记载来看,鲜卑发展骑射活动的条件是比较优越的。按《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鲜卑》:“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从这条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鲜卑盛产大量优质的马匹,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离不开马、牛、羊等牲畜,这为鲜卑人锻炼自己的骑射能力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使他们几乎可以从小就对骑马产生浓厚兴趣。鲜卑人还发明了极具民族特色的骑射工具,即“角端弓”,这种以牛角为原料制作的弓,因其原料易于获取且结实耐用,从而保证了鲜卑人对弓箭需求的供给。另前文引《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乌桓》中记载了乌桓人可以自行制作弓矢鞍勒,并可以锻金铁为兵器,汉代的鲜卑人应该也是如此,掌握了熟练的制作骑射工具的技能。
骑射在早期鲜卑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汉代的鲜卑是一个游牧民族,其社会发展尚处于部落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有限,几乎不太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狩猎成为他们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生产方式和食物来源。在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中曾发现有刻着猎人射鹿图像的骨饰板以及雕有羊形状的羊形饰牌,充分说明了狩猎在鲜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从东汉中后期开始,随着鲜卑在汉王朝北方草原地区的逐步扩张,势力愈发壮大,人口逐渐增多,但其生产力发展相对中原地区而言,大幅度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过度依靠游牧与狩猎的经济模式使鲜卑社会出现了“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的情况,因此,不得不“东击倭人”开发捕捞业以补充粮食不足。但无论狩猎、游牧还是捕捞,从根本上来看,仍然是一种粗放的生产方式,在生产效率上也很难满足鲜卑人对粮食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随着鲜卑的扩张,他们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与深入,不断有其他民族的人口被掳掠并充实到鲜卑部族之中去,鲜卑逐渐变成了一个族源复杂的部落集团。在这一与外族频繁接触的过程中,很多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被引入鲜卑社会之中,尤其是东汉时期的鲜卑曾经掳掠了大量的汉族人口,以及与汉族关系十分密切的像高句丽等族的人口,并与他们进行了频繁而深入的交往,使中原地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逐渐被鲜卑接受,并潜移默化地改造鲜卑社会。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鲜卑》载,曹魏“黄初二年,比能出诸魏人在鲜卑者五百余家,还居代郡”。说明东汉至曹魏时期的鲜卑,经常掳掠汉族以充实其社会人口。又如十六国前燕慕容鲜卑社会,八王之乱后“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从慕容廆时期开始,慕容氏即对中原流民采取蓄意引纳,“禀给遣还,愿留者即抚存之”,因而“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至慕容皝时,仅辽西即“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使慕容氏治下汉族人口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鲜卑族,其中亦不乏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这些汉族人为慕容鲜卑社会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文明,农耕经济迅速成为其社会的主要经济模式,儒家文化也在慕容鲜卑社会中迅速铺陈开来,以至“路有颂声,礼让兴矣”。诚如魏收所云:“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至北魏时期,鲜卑文化则完成了与汉文化相交融的过程,鲜卑民族本身逐渐与汉民族融为一体,鲜卑民族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社会阶级组成以及尚保留的一些鲜卑民族传统外,其余方面已经与汉族社会没有不同。在这一过程中,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自然也随之产生了转变。
二 鲜卑的军事体育文化
除狩猎外,骑射对于鲜卑人而言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鲜卑崇尚武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很多生活必需品都难以自给自足,因此外出劫掠成为他们获取生活物资的一个重要途径。东汉时期的鲜卑,随着自身实力逐渐发展壮大,开始不断地对外征伐,针对汉王朝北方边郡的劫掠非常频繁。据《后汉书·和帝纪》载,仅和帝一朝,永元年间,鲜卑先后寇肥如、右北平、渔阳等地,辽东太守祭参因之下狱而死;又如灵帝时,据《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建宁元年)十二月,鲜卑及 貊寇幽并二州。”“(建宁二年)十一月……鲜卑寇并州。”“(建宁四年)冬,鲜卑寇并州。”“(熹平元年)十二月……鲜卑寇并州。”“(熹平二年)冬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熹平三年)十二月,鲜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击破之。鲜卑又寇并州。”“(熹平四年)五月……鲜卑寇幽州。”“(熹平五年)十二月……鲜卑寇幽州。”“(熹平六年)夏四月……鲜卑寇三边。”
貊寇幽并二州。”“(建宁二年)十一月……鲜卑寇并州。”“(建宁四年)冬,鲜卑寇并州。”“(熹平元年)十二月……鲜卑寇并州。”“(熹平二年)冬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熹平三年)十二月,鲜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击破之。鲜卑又寇并州。”“(熹平四年)五月……鲜卑寇幽州。”“(熹平五年)十二月……鲜卑寇幽州。”“(熹平六年)夏四月……鲜卑寇三边。”
八月,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鲜卑,晏等大败。……十一月……鲜卑寇辽西。“(光和元年)十二月……鲜卑寇酒泉。”“(光和二年)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光和三年)冬闰月……鲜卑寇幽、并二州。”“(光和四年)冬十月……鲜卑寇幽并二州。”“(中平二年)十一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鲜卑的内寇,多以骑兵突袭的形式进行,得手之后随即在汉人步兵未及反应之前撤退,不以获取领土为目的,即所谓“寇抄”(又作“寇钞”)。鲜卑寇抄之频繁,使“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东汉年间,如辽西、代郡、云中、玄菟、雁门、定襄、渔阳、高柳、朔方、辽东、幽州、并州、凉州等地,皆多次遭到鲜卑入侵劫掠。檀石槐掌权后,鲜卑更是“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鲜卑成为汉王朝北方最大的边患,而到了轲比能时,鲜卑则“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
这种类似后世游击战一般的寇抄劫掠,对骑射技能要求非常之高,非弓马娴熟、武艺高超的军队不能为之。鲜卑也正是凭借其强大的骑兵军队,击破了匈奴,雄踞漠北。而强大的骑兵,如果没有平时频繁而系统的骑术训练和军事技能训练,是不可能形成的。
在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六国时期,随着鲜卑社会的日益稳定繁荣,社会结构逐渐转型,鲜卑人传统的骑射体育也有了新的发展。按《魏书》记载,十六国时期代国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建国五年(东晋咸康八年,342):“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讲武,即讲习武事。《国语·周语上》:“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韦昭注:“讲,习也。”故“讲武”者,实乃“讲”“习”结合,以“习”为主,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军事操练。随着战争的需要及最高统治者对军事的重视,讲武上升为御驾亲临的军事检阅及操练的礼仪活动。这是在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关于鲜卑国家层面官方骑射训练的记载,透露出以下几点比较重要的信息。
第一,随着汉末檀石槐一统鲜卑各部,又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鲜卑的社会结构日趋稳定,政治上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社会向心力增强,因此鲜卑从国家整体层面开始推进社会文化的建设与巩固。第二,在这一背景下,骑射作为鲜卑社会中最有传统的一种社会文化、体育文化,开始得到统治者更进一步重视。讲武驰射成为鲜卑社会一种定期举行的集会与训练模式,说明骑射训练已经成为鲜卑社会的官方国家战略,骑射已经不仅仅是鲜卑社会民间盛行的文化样式,更得到了统治阶层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动。第三,我们还应注意到,以官方定式的形式,将讲武与骑射并行不悖,这固然是在鲜卑人尚武民风深刻影响下的产物,更说明军事操练与骑射开始被鲜卑人有意识地结合,从而使鲜卑的骑射体育产生全新的内涵。
自此之后,在有关鲜卑的文献记载中开始频繁出现这种由统治阶层推动的讲武骑射活动,尤其是北魏时期。如北魏道武帝登国六年(391):“秋七月壬申,讲武于牛川,行还纽垤川。”明元帝永兴二年(410):“秋七月丁巳,立马射台于陂西,仍讲武教战。”太武帝始光三年(426):“秋七月,筑马射台于长川,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绘絮各有差。”始光四年(427):“秋七月己卯,筑台于祚岭,戏马驰射,赐射中者金锦绘絮各有差。”太延五年(439):“秋七月己巳,车驾至上郡属国城,大飨群臣,讲武马射。”文成帝兴安二年(453):“秋七月辛亥……筑马射台于南郊。”和平四年(463):“秋七月壬午,诏曰:‘朕每岁以秋日闲月,命群官讲武平壤。所幸之处,必立宫坛,糜费之功,劳损非一。宜仍旧贯,何必改作也。’”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春正月……己酉,讲武于唐水之阳……三月辛酉朔……讲武于云水之阳。”太和十八年(494):“八月……丁未,幸阅武台,临观讲武。”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种以君主为首进行的讲武骑射活动的频繁出现,说明了鲜卑统治者对之的高度重视,武术与骑射已经不仅仅是以民风、民俗的形式出现在鲜卑社会中,更是被统治者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加以推广。
骑射、讲武以及武术,应该是早期鲜卑最为重要的军事体育活动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武术”,还没有发展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注重武德修养和内外兼修,具有套路、对抗、功法等多种运动形式与传统文化内涵的民族体育”这一形式。它应该还仅是古代军事技击术的层面,是“武术”产生的初级阶段。魏晋时,陈寿在《三国志》中用“武艺”这个词,对当时所有的包括习战射、晓五兵、舞剑戟等武技进行概括;宋元时,“武艺”发展为“十八般武艺”;而“武术”一词在民国初年才定名,发展至今,“武术”则是一个包含技击术又高于技击术这样一个包容性很强的词。本书中所说“武术”,更为确切地说应是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说的“武艺”,只是我们按现在的统一称谓而写作“武术”。
三 鲜卑的射箭体育文化
随着鲜卑对汉文化的接触与了解愈加深入,鲜卑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至北魏孝文帝时期更是开始其全面汉化的进程,到了隋唐时期,鲜卑则已经与汉族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儒家文化对鲜卑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鲜卑的射箭体育文化也与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在一起了,其文娱性、竞技性愈发显现,现仅就射箭而言,加以阐释。
射本为儒家六艺之一,如《周礼·保氏》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射在先秦时期既是一种战争技术,又是一种选拔武士的礼,在很多仪式中存在射礼,其流传非常久远。射的渊源最早应该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人类的狩猎活动,商代时即已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战争和军事训练中了,到了西周以后则被人们进一步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义。按《礼记·射义》:“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者,莫若射”,可知商周时的射礼已经成为人们修养德行的重要途径,在“礼”这一社会秩序规则中有着重要意义。《礼记·射义》认为:“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可见儒家知识分子认为射箭这种活动非常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修养身心的方式,从而使射箭“摆脱了外在修饰的色彩而转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射箭作为一种具备较强竞技性的礼仪活动,在商周至汉都非常流行,其类型有祭祀时进行的大射、天子宴飨诸侯时的宾射,于燕息时进行的宴射,普通百姓可以参与的常与乡酒之礼同时进行的乡射,在社会中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皆十分流行。
自鲜卑南下中原之后,这种射礼活动在鲜卑社会中开始频繁出现。“作为竞技的射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朋射和单射两种形式。”其中朋射是一种团体性质的射箭比赛,参赛者一般要分成两队,按双方各自射中的箭数记筹,筹数多者为胜,这种射箭比赛在北魏时期经常举行。如《北史·魏诸宗室》记载:“初,孝武在洛,于华林园戏射,以银酒卮容二升许,悬于百步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顺发矢即中,帝大悦,并赏金帛。顺仍于箭孔处铸一银童,足蹈金莲,手执划炙,遂列背上,序其射工。”又《魏书·道武七王传》载:“浑好弓马,射鸟,辄历飞而杀之,时皆叹异焉。世祖尝命左右分射,胜者中的,筹满,诏浑解之,三发皆中,世祖大悦。”类似的记载尚有多处,说明朋射在鲜卑的上层社会中已经是非常流行的竞技与娱乐方式。单射作为一种单人进行的射箭活动,也是北朝时期鲜卑人喜爱的射箭竞技活动,《北齐书·元景安列传》载:“肃宗曾与群臣于西园宴射,文武预者二百余人。设侯去堂百四十余步,中的者赐与良马及金玉锦彩等。有一人射中兽头,去鼻寸余。唯景安最后有一矢未发,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仪,操弓引满,正中兽鼻。帝嗟赏称善,特赉马两匹,玉帛杂物又加常等。”类似的有关单射活动的记载同样并不罕见。从这些记载来看,与汉族的射礼相比,鲜卑的射箭活动更加富有文娱色彩。
朋射与单射在北朝鲜卑社会中的流行,充分说明鲜卑人已经将其有着悠久传统的射箭文化与儒家的射礼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是儒家思想在鲜卑社会中深入传播的结果。这种结合使鲜卑的射箭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形式更为多样,娱乐性、竞技性得到了加强,更使射箭在其原本作为生产技能、战争技能而存在的意义上,具备了更多、更深入的文化内涵。
四 鲜卑的其他体育文化
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鲜卑人生活地域的逐渐南移,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越来越深入,鲜卑的社会生活开始趋于稳定,其传统的游牧生活逐渐为农耕定居生活所取代,社会经济与政治都在根本上发生了转型,开始向汉族靠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鲜卑社会中的体育文化也产生了变化,体育活动不再局限于骑射及由骑射而衍生的传统活动项目,而是出现了很多新内容,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其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这在之前的文献资料中是不曾体现的。
黄聪先生曾考证了北朝时期鲜卑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体育活动,除最为传统的骑射外,还有登山畋游、围棋、投壶与击壤、樗蒲与握槊、赛马、速跑、跳绳,以及百戏中的一些活动如角抵、高 百尺、长
百尺、长 、缘橦、跳丸、五案等体育项目,在此分别予以介绍。
、缘橦、跳丸、五案等体育项目,在此分别予以介绍。
(一)登山畋游
登山畋游,即爬山田猎活动,目前文献资料中所见最多的,就是北朝时期帝王世家的登山田猎活动。据笔者统计,仅北魏文成帝一朝,关于文成帝登山畋游的记载就多达20余处。如兴安二年(453):“夏五月乙酉,行幸崞山”,“秋七月辛亥,行幸阴山……筑马射台于南郊”,“冬十有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观察风俗”;兴光元年(454):“夏六月丙寅,行幸阴山”,“冬十有一月……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太安元年(455):“夏六月……戊寅,帝畋于犊倪山”;太安三年(457):“春正月壬戌,畋于崞山”;“夏五月庚申,畋于松山”;“六月癸卯,行幸阴山”;“八月,畋于阴山之北”。太安四年(458):“春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禁。乙卯,行幸广宁温泉宫,遂东巡平州。庚午,至于辽西黄山宫,游宴数日,亲对高年,劳问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于山下,班赏进爵各有差。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戊寅,南幸信都,畋游于广川。”“三月丁未,观马射于中山。”“六月丙申,畋于松山。”“冬十月甲戌,北巡。至阴山……辛卯,车驾次于车轮山,累石记行。”太安五年(459):“六月戊申,行幸阴山。”和平二年(461):“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三月……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和平三年(462):“二月癸酉,畋于崞山,遂观渔于旋鸿池。”“夏六月庚申,行幸阴山。”和平四年(463):“五月……壬寅,行幸阴山”;“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和平五年(464):“六月丁亥,行幸阴山。”
从以上诸多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登山畋游,是北魏帝王十分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开展得十分频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活动除了满足帝王本人的娱乐需求外,还经常被其赋予一定的政治意义。如《魏书·高宗文成帝纪》即记载,和平四年(463):“八月丙寅,遂畋于河西。诏曰:‘朕顺时畋猎,而从官杀获过度,既殚禽兽,乖不合围之义。其敕从官及典围将校,自今已后,不听滥杀。其畋获皮肉,别自颁赉。’”由登山畋游之所见所感而引申出政治措施,可知这一活动往往被帝王作为体察民情疾苦的手段,并由此可知这一活动在北魏政治生活中自有其特殊的功能。
(二)围棋
十六国北朝时期鲜卑社会中的围棋活动盛行。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曾有如下故事:
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太半,以赐贫人。弼览见之,入欲陈奏,遇世祖与给事中刘树棋,志不听事。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乃起,于世祖前捽树头,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世祖失容放棋曰:“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弼具状以闻。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性。弼曰:“为臣而逞其志于君前者,非无罪也。”乃诣公车,免冠徒跣,自劾请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闻筑社之役,蹇蹶而筑之,端冕而事之,神与之福。然则卿有何罪?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民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太武帝因下棋竟险些耽误政事,可见统治阶层对围棋之痴迷。又如北魏孝文帝时有中山人甄琛,《魏书》对其有如下记载:
入都积岁,颇以弈棋弃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苍头常令秉烛,或时睡顿,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后不胜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辞父母,仕宦京师,若为读书执烛,奴不敢辞罪,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而赐加杖罚,不亦非理!”琛惕然惭感,遂从许睿、李彪假书研习,闻见益优。
甄琛嗜棋如命,日夜不休,直至奴仆当头棒喝方幡然醒悟,足见围棋在当时文人士子阶层的风靡。
(三)投壶与击壤
投壶与击壤,皆为源自中原的体育活动,至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相传投壶起于战国之时,而“击壤”则更为早一些,这从“帝尧之世,击壤而歌”的典故中可以看出。
投壶,是一种传统礼仪和宴饮游戏,据郑玄注《礼记·投壶》:“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又宋人吕大临《礼记传》云:“投壶,射之细也。燕饮有射以乐宾,以习容而讲艺也。”可知投壶实际上是古代射礼的一种替代礼仪,因射礼具备一定的危险性,且需要相对广阔的场所,并非各种场合皆能举行,也并非所有参与者都能接受,因此产生了投壶这种相对温和的活动。投者,投掷也,投壶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分宾主将手中四支无镞之矢投入壶中,以为礼仪、娱嬉。
南北朝时期的投壶活动,比春秋战国时期要复杂得多,据《颜氏家训》记载:
投壶之礼,近世愈精。古者,实以小豆,为其矢之跃也。今则唯欲其骁,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带剑、狼壶、豹尾、龙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莲花骁。汝南周碷,弘正之子,会稽贺徽,贺革之子,并能一箭四十余骁。贺又尝为小障,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所失也。至邺以来,亦见广宁、兰陵诸王,有此校具,举国遂无投得一骁者。
其中记载了南朝梁、陈二国的投壶形式,尤以周碷、贺徽技术最高,并发明了新的规则。而这种演化了的投壶活动,已经被传入北朝社会。北齐神武帝高澄之子高孝珩、高孝瓘收藏有这种改进后的投壶器具,可知北齐的鲜卑化汉人统治阶层对这种活动是相当熟悉的。
击壤,一般认为是中国古代一种以土块击打土块类型的游戏,相传尧舜时就已经出现,据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魏晋时曹植亦在其名赋《名都篇》记载道: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鲐虾,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
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这里的“击鞠壤”,就是“击鞠和击壤”的意思,可知击壤活动源远流长。
至北魏时,击壤活动仍然盛行,据《魏书·宣武帝纪》记载,永平三年(510):“诏曰:‘朕乘乾御历,年周一纪,而道谢击壤,教惭刑厝。’”可知北魏帝王阶层在当时对击壤活动十分重视,而且击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还兼具劝民教化的作用。
(四)樗蒲与握槊
樗蒲,亦作摴蒲、摴蒱,又名蒲戏、捕博,是中国古代博戏的一种,因博具中用于掷采的骰子最初用樗木所制而得,其在中原地区出现甚早。十六国北朝时期,这种博戏已经在鲜卑社会中十分流行。如后燕时烈宗慕容宝即擅长樗蒲,据《晋书·慕容垂载记》:“宝在长安,与韩黄、李根等因宴樗蒱,宝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摴蒱有神,岂虚也哉!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于是三掷尽卢,宝拜而受赐,故云五木之祥。”又如北魏时张僧皓:“尤好蒲弈,戏不择人,是以获讥于世。”可知樗捕活动在鲜卑社会中是广泛流行的。
握槊,在古代是一种类似双陆棋的博戏,是一种棋盘游戏,以掷骰子的点数决定棋子的移动步数,首先把所有棋子移离棋盘者即可获得胜利。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代的握槊游戏应该源自西域。据《魏书·术艺传》记载:“此盖胡戏,进入中国,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将杀之,弟从狱中为此戏以上之,意言孤则易死也。世宗以后,大盛于时。”说明握槊并非源自中国的体育活动,其当从西域传入中原,又从中原传入鲜卑。
握槊在北朝时期的鲜卑社会是有所流传的,如“高祖时……赵国李幼序、洛阳丘何奴并工握槊”。又北魏末年,鲜卑贵族尔朱世隆即十分喜爱握槊之戏,据《魏书·尔朱彦伯列传》记载:“世隆曾与吏部尚书元世俊握槊,忽闻局上歘然有声,一局之子尽皆倒立,世隆甚恶之。”可知握槊在鲜卑社会是流传甚广的。
(五)跳绳
跳绳,这种游戏在唐朝时称“透索”,宋朝时称“跳索”,明朝时称“跳百索”“跳马索”,清末后才称为“跳绳”。最早出现的跳绳史料是汉代画像石上的跳绳图,说明至迟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跳绳活动。据《北齐书·幼主纪》载:
初河清未,武成梦大猬攻破邺城,故索境内猬膏以绝之。识者以后主名声与猬相协,亡齐征也。又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
这条记载说明,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为形式的跳绳活动,在北齐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北齐虽不是本书的研究范畴,但北齐作为一个鲜卑化的汉人政权,其治下鲜卑人口众多,那么,这种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在鲜卑族群中有所流行也是十分可能的。
(六)百戏
百戏,本为中原地区汉族民间表演、杂技艺术的泛称,一般认为当源自先秦时期的“讲武之礼”和公卿贵族节日宴庆的表演。春秋战国时期,原本作为军事训练和礼制教育的“讲武之礼”,后逐渐演变为“以为戏乐,用相夸视”之用,成为国君和公卿贵族们节庆宴会上的娱乐表演。当时在上层社会的宴席聚会上不仅有各种乐舞表演,还有舞剑、角力(举重一类表演)、角抵(类似摔跤)、斗兽等表演活动,至汉代则进一步丰富起来,其内容基本包含了各种娱乐消遣、杂耍和健身类活动。
北朝时期,百戏活动被传入鲜卑社会中。据《魏书·乐志》记载,北魏道武帝天兴六年(403):“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抵、麒麟、凰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 百尺、长
百尺、长 、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这条记载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百戏活动内容,说明鲜卑人对百戏活动的接受是全面而完整的,基本全面复制了汉民族百戏活动的形式。
、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这条记载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百戏活动内容,说明鲜卑人对百戏活动的接受是全面而完整的,基本全面复制了汉民族百戏活动的形式。
我们应该注意到,上述这些体育活动,很多并非源生于鲜卑社会中,而是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如投壶与击壤,这两项活动最早在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了。又如围棋,中原地区古时称“弈”,最早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在历史记载之中。又如百戏,本为中原地区汉族民间表演艺术的泛称,按宋人高承《事物纪原》百戏条引《梁元帝纂要》云:“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后乃有吞刀、高 、履火、寻橦等也。”说明其自秦汉时期即已有之。这些活动都是鲜卑民族与汉族大规模接触之后才开始在其社会中出现的,汉文化在改变鲜卑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为鲜卑的体育文化带来了很多全新的内容,使鲜卑体育活动的内涵与外延、意义与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履火、寻橦等也。”说明其自秦汉时期即已有之。这些活动都是鲜卑民族与汉族大规模接触之后才开始在其社会中出现的,汉文化在改变鲜卑民族文化的同时,也为鲜卑的体育文化带来了很多全新的内容,使鲜卑体育活动的内涵与外延、意义与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北朝鲜卑的统治阶层也在不断地推动这种体育文化的融合与转型。如道武帝时即将本为汉族体育文化内容的百戏等活动在鲜卑社会中自上而下地进行推动,甚至成为宗庙定制,说明鲜卑体育文化的这种转型,是在统治者有意识的推动之下逐渐成型的,而这也是自汉末时期即已开始的鲜卑汉化进程所导致的一种历史必然。
(七)乐舞
鲜卑人还经常进行乐舞活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乌桓》载乌桓“至葬则歌舞相送”,而鲜卑亦经常进行大规模的集会活动:“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由于两族在风俗习惯上的相似,所以鲜卑应该与乌桓一样,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大规模的集会宴舞应该是鲜卑人经常进行的文娱活动,而舞蹈也是早期鲜卑人比较钟爱的一种体育活动形式。
五 鲜卑体育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从春秋战国至南北朝,在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鲜卑民族的体育文化完成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转型,在形式与文化内涵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转型之彻底,推行之坚决,不仅在东北民族之中,在中国历史上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所有民族间都是罕见的。在这种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北朝鲜卑相比于其早期社会,体育文化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全民性的、社会性的,其根基在于鲜卑民族文化的转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鲜卑人关于体育的观念也产生了变化,正是这种坚决而彻底的转型,使鲜卑的体育文化融入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汉族文化,从而使鲜卑的民族传统体育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我们还发现,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鲜卑人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在其社会中推动体育文化的发展。在早期的鲜卑社会中是存在以骑射为代表的体育活动的,但这些体育活动往往并不是单纯地以身体教育为目的,反而更多以民风、民俗乃至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形式体现出来,是一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社会群体行为。而随着鲜卑社会发展的进步,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鲜卑人,尤其是鲜卑社会的统治阶层,开始有意识地在其社会中对多种类型的体育活动进行推广,鲜卑体育活动的内涵与外延都扩展了,这说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鲜卑人对于体育在社会精神文化中的作用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鲜卑体育,开始更加注重体育的竞技功能,如射箭、击壤等竞技活动在这一时期的鲜卑文献中开始大量出现,这在以往的资料中是没有的。激烈的对抗性与竞争性是竞技体育区别于大众体育最为本质的特征,竞技体育通过这两点来吸引竞技者的参与和民众的关注。竞技体育在鲜卑社会中的大量出现,说明体育在鲜卑社会中已经开始了其休闲化、文娱化的历史进程。
鲜卑的体育文化转型,从过程来看,其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第一,鲜卑的体育文化转型,是自上而下的,是全民参与的,是社会性的。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普通百姓,都积极而富有热情地参与到这次转型过程之中。这种转型既有将讲武骑射列为定制的从官方层面自上而下的推行,也有将投壶、击壤等他族文体活动融入鲜卑社会的自发于普通百姓之间的社会性运动。因此,鲜卑的体育文化转型既是官方推动的,又是民众自发的,其转型之彻底与坚决,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没有这种全民性的参与,这种转型必然不会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二,鲜卑的体育文化转型,不仅仅是单纯的体育活动内容的改变与丰富,更是一场发生在文化层面上的转型运动。不断地向先进文化汲取营养,吸收和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体育文化,是这场转型运动得以成功的文化保障。鲜卑的传统文化是游牧文化,而汉民族则是农耕文化、儒家文化,从文化发展层面的角度来看,中原文化相对于鲜卑文化来说毫无疑问属于先进文化。相比于鲜卑文化,汉文化在文化的内容上要更为丰富,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强,对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更加有力。而相比于汉文化,传统的鲜卑文化则显得相对原始,其文化土壤也相对贫瘠,对于其社会文化的理论总结与探索则近乎为零。我们知道,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相对落后的文化向先进文化进行学习、借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之一,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自然选择。而鲜卑人正是在与汉族社会交流、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将汉文化中的精髓成分有意识地推介、引入自身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地试图缩小乃至消灭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差距,才最终迎来了鲜卑社会文化的大发展。而体育文化,毫无疑问是这场文化转型的受益者。
第三,对汉文化的学习与借鉴,非但没有使鲜卑的民族传统体育走向没落,反而促使其有了全新的发展,在新的社会形态与历史背景下焕发出了勃勃生机。鲜卑人最为传统的体育活动就是骑射,我们知道,骑射在草原文化中更多是作为一种生存技能和生产方式而存在的,其生产功能要大于文化功能。而自鲜卑迁至中原地区居住之后,骑射游牧很显然不再适合担当社会主要生产方式的重任,向农耕生产转变是鲜卑人理应做出的历史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骑射的社会功能的重要性显然下降了,其作为一种传统体育似乎开始面临危机。但事实上,在鲜卑人后续的发展中,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在与汉文化的接触中,鲜卑人将儒家文化中的射礼与自己的骑射传统充分地结合起来,使射箭的形式更加多样,朋射、单射这种儒家射艺中比较常见的竞赛方式被广泛传播,并且往往与传统的骑射结合在一起进行,从而使射箭活动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骑射体育非但没有逐渐没落,反而以全新的面貌愈加繁荣。
©️本文版权归作者【先晓书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