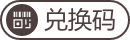-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新书推荐 |《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试读
作者:汤姆·霍兰
来源:甲骨文
发布时间 2020-11-24 10:30 浏览量 202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奥维德惊恐地发现,自己来到了托米斯。这座城市和他的风格毫不相符,是由先前的希腊殖民者开拓而成的,坐落在寒凉刺骨、狂风呼啸的黑海海岸上,地处罗马势力范围的边缘。奥维德抱怨托米斯只有漫无尽头的冬天。尽管这话夸张过了头,但此地夏季温和宜人的气候也没能缓解他的抑郁情绪。
很难想象还有比它更不像罗马的城市了。水是咸味的,食物也糟糕透了。这里没有人说拉丁语,托米斯人所说的希腊语也让奥维德觉得跟胡言乱语无异。四周树木稀少,满目荒凉,刹那间,世界首都的乐趣在他的记忆中灼灼闪烁,有如幻影。“在这儿,”他悲戚地反省道,“反倒是我成了野蛮人。”
论时尚,奥维德的品位不输罗马任何一人,但此刻,他身边的行省居民居然连自己有多偏狭土气都意识不到,这令他震惊万分。低矮倾颓的托米斯堡垒内,没人能体会并分担他对都市时尚的痛苦思念。城墙外的世界更是野蛮。北面约70英里处就是多瑙河。
在恺撒及其战略家的地图上,这代表着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那宽阔的河面足以阻挡潜伏于对面的野蛮人的入侵;但实际情况出入很大。冬季,连三角洲外的海面都可能结冰,多瑙河河水自然也会牢牢凝固;这时候,河对岸原野上的蛮族就会骑着快马出现,他们胡须结满白霜,掠夺成性且绝不手软。
缕缕青烟从阴沉的天际袅袅升起时,意味着村庄已经付之一炬。身中毒箭的尸体形状扭曲,而身背行李的幸存者则由绳索或铁链拴着,在野蛮人的驱赶下蹒跚前行。噩梦中,奥维德常常梦见自己在躲避飞箭或被困棺材,醒来时发现房顶插满了箭矢。
每每望向托米斯城墙外围攻的蛮兵,他便感觉自己有如瓮中之鳖。罗马似乎不止遥望无垠,还软弱无能。“她是那样的美轮美奂,但绝大部分人几乎留意不到她的存在。”对奥维德这样热衷都市生活的人而言,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他们不畏罗马人的武力。”
但他的焦虑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奥维德看来,托米斯人和城门口的野蛮人并无二致。男人身穿羊皮裤,浑身毛茸茸的,难以形容;女人则将水罐放在头上。数世纪来,罗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生活的。
犹记得生活在繁华文明的大都市时,他还嘲笑第一公民对罗慕路斯时代的追忆,把第一代罗马人称作杀人犯、强奸犯和畜生。如今迁到世界尽头,他不禁感到自己仿佛也被流放到远古时代了。踟蹰在文明和野蛮的边界,奥维德深感自己生活在一个半人半兽甚至更糟糕的国度。他抱怨道,他们比“狼还野蛮”。
搁浅在这罗马势力范围的边缘,他凝望远方,只见一片黑夜漫漫无垠。他能感受到这种黑暗的广大和强大,能感受到它对自己一切身份的不屑一顾。难怪,在注意到居民们所说的退化的希腊语时,他开始担忧自己可能说不好拉丁语了。
野蛮主义也同样潜伏在罗马人体内。毕竟,罗马城的缔造者就吸吮过狼奶。在汩汩喷涌的喷泉兴起以前,在供时尚人士乘凉的门廊被建造出来以前,罗马的人们就“曾像野兽一样活着”。奥维德知道,罗马也曾是世界的一片黑暗之地。
或许只有远离都城风月场,来到文明的边缘后,才能真正了解罗马自远古以来的不朽发展进程,才能真正明白自己民族伟大的根源。自“流放到一片法治基础薄弱的边境地带”后,奥维德的时尚热情被第一公民带来的残酷真相狠狠嘲弄了一番。没有战争的胜利,便没有和平的艺术。
归根结底,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不在于完善的排水沟,也不在于光彩夺目的神庙,更不在于对诗词歌赋的喜好,而是钢铁:军队列好阵、举着护盾进击所需的钢铁纪律。尽管罗马人曾由狼哺育,但他们手起刀落的娴熟并非源自兽性。严苛残酷的训练已将他们锻造成战斗链中的一环。
战士不能娶妻生子,战友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切。军团不是一群动物,更像一台杀人机器。战士们敬奉玛尔斯为“前行者”。是他赐予了他们勇气,让他们迎着激烈的号角声整齐划一地行进,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和那连续沉重的步伐相对的,是敌人渺茫的胜利希望。即便最野蛮嗜血的蛮兵在向一支罗马军发起冲锋时,都极可能功亏一篑。多瑙河对面的野蛮部族习惯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刻有如飞鸟俯冲而来”。
与他们不同的是,罗马军队在耐力方面饱经历练。罗马士兵所受的训练为任何情况下都要直击对手要害,然后拾起步伐再度前进,继而浑身是血地再次直面敌人。若非如此,他们杀戮嚣张不敬之辈的本领也就不可能这般强大了。“是纪律,严格的军纪真正保卫了罗马的势力。”
一切皆来源于纪律:面对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在机会渺茫的情况下,仍坚忍不拔地追求胜利;在反反复复的逆转和叛乱中锲而不舍、矢志不移。出乎奥维德意料的是,在他抵达托米斯时,巴尔干半岛已不再是想象中桀骜不驯、威胁重重的荒凉之地,而是几乎已完全服帖了。这一驯服过程是漫长而艰巨的。
自渴望建功立业的屋大维宣布平定伊利里亚,以及十年后克拉苏击溃巴斯塔奈人以来,数十载光阴已穿梭流逝。最伟大的功勋莫过于提比略在退隐罗德岛前平定了现今的匈牙利,那里有野猪和更野蛮的部落出没。这些部落的成员被称作潘诺尼亚人,在与罗马的抗争中展现出了深入骨髓的反抗精神。
公元6年,当地不时爆发的反叛林火形成了一场恐怖的大火灾。商贩被屠杀,分遣队被全歼,马其顿被入侵。连第一公民都在这场毁灭性的叛乱面前慌了阵脚。他歇斯底里地向元老院警告道,若不采取紧急措施,潘诺尼亚人十天后就将兵临罗马城下。好在罗马最厉害的将军已从罗德岛归来,可供第一公民再次号令差遣。
耐心冷酷的提比略是领兵应对游击战的完美人选。他关心士卒的福祉,也同样留意遭受伏击的潜在危险。尽管都城屡屡厉声追索战果,但他充耳不闻。他所追求的是慢和稳。“在提比略看来,安全之道才是上策。”
历经数周乃至数月的较量后,提比略最终大败潘诺尼亚人。公元8年,潘诺尼亚人终于缴械投降,在河岸边成群地对这位胜利大将军匍匐称臣。第二年,当奥维德还在因首次见到野蛮人而吓得发愣时,烈火和杀戮已经在向巴尔干地区最后一个群山中的反叛据点蔓延。
年轻的日耳曼尼库斯第一次领兵作战,然而事实证明,他虽然富有魅力但作战能力非常有限。提比略接过任务后给了敌人致命一击。此地终于被完全平定了。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从马其顿到多瑙河,一大片疆土收归罗马统治之下。提比略得到了第一公民的诚挚感激和同胞们的热情赞赏。“胜利女神在罗马大将军的头上扑打着翅膀,将月桂花环戴在他的亮发上。”
但任务尚未结束。不止奥维德一人注意到:多瑙河对面的野蛮部族完全能够穿越磅礴的水流。哪怕最强大艰险的自然屏障都能被跨越。这对守护边疆的将士来说无疑意味着刺激和麻烦。
罗马人最引以为豪的一点在于,他们并非为征服而征服。他们冲锋陷阵,不是因为贪婪或嗜血,而是为了捍卫城市荣誉和盟友利益。可以说,他们是在保家卫国的路上征服了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罗马政治家看来,“或许把我们的全球统治霸权叫作护国政权更为恰当”。
若非如此,天神又怎么可能让罗马成就千秋伟业呢?当然,这是一个设问句。整个世界如若置身罗马的监护之下,无疑会变得更加美好。奥古斯都主宰的光荣持久的和平岁月,用他自己的狂言傲语来说,取决于“四海皆朝服于罗马人民的统治”。当然,恰如那些望向多瑙河对岸的人所意识到的那样,事实上,要实现四海朝服,罗马仍有一段路要走。
但罗马的上层阶级越发深信,那一天终将到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将受益。抱负和责任在催他们奋进,更不用说的是,他们也遵从不言自明的神谕,这一切都推动着罗马继续向外扩张。终极奖赏——“无边无际的帝国”就在前方。
本文摘自《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作者是汤姆·霍兰(Tom Holland),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多部畅销作品,尤其擅长古希腊罗马历史写作。《王朝》一书的前作《卢比孔河》(Rubicon)获塞缪尔·约翰逊奖提名,并荣获2004年赫塞尔-蒂尔特曼历史学奖,《波斯战火》(Persian Fire)获2006年朗西曼奖。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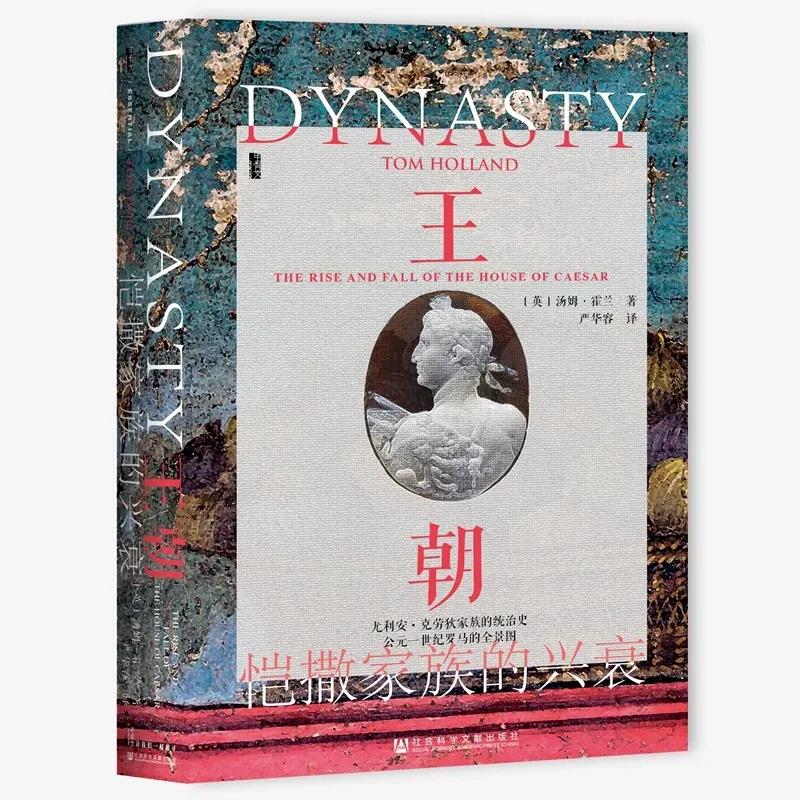
王朝:恺撒家族的兴衰
[英] 汤姆·霍兰 著 | 严华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 2020年10月
汤姆·霍兰试图以叙述史的形式填补史料与传闻之间的空白,帮助我们在轻信与过度质疑之间开辟一条追溯尤利安·克劳狄王朝历史的全新路径。从奥古斯都、提比略、卡利古拉到克劳狄乌斯和尼禄,这个家族主宰罗马的岁月是一个漫长的试验期,每个皇帝都在试探权力的边界。提比略从伟大的将帅转变为愤世嫉俗的隐士,卡利古拉骑马跨海、寻欢作乐,而尼禄则通过弑母之罪将自己打造为悲剧英雄。
在《王朝》这幅描绘罗马第一王朝的画卷中,霍兰将寻找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或是这些谣言背后的创作动机,生动还原这个关于统治与毁灭的故事。
©️本文版权归作者【先晓书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