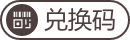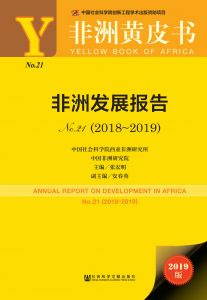-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非洲族群冲突的新特点、新趋势及驱动因素
作者:张宏明 ,安春英
来源:《非洲发展报告No.21(2018~2019)》
发布时间 2020-01-07 14:43 浏览量 333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当代非洲武装冲突大致可以分为国家间战争与“社会战争”(societal war)两类。国家间战争主要包括反对欧洲殖民政府的独立战争和非洲国家间战争。在获得独立后,大约一半的反殖民战争沦为内战;非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数量不多,大都规模小且短暂,主要涉及领土或跨境问题。从持续时间、规模和影响来看,社会战争是“非洲式暴力冲突”的主要形式。社会战争依据战争的动员方式,即根据族群身份或政治意识形态(革命)的视野进行分类。两者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冲突群体的构成以及挑战国家权威的意图。族群冲突的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特定的社会认同群体,该群体期望占有更多资源,或达成自治甚至分离主义的目标,从而与国家和其他群体对抗。卡尔·科德尔(Karl Cordell)和斯蒂芬·沃尔夫(Stefan Wolff)认为族群冲突是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冲突爆发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冲突的断层线依托族群差异或边界,至少有一个冲突当事方从族群的角度解释其不满。也就是说,冲突一方认为由于其族群身份而无法满足其诉求,得不到相应的权益,于是围绕族群身份组织对抗。因此族群冲突指的是“在一定意义上族性作为一种外显或内在因素的冲突”。
自20世纪60年代非洲殖民地陆续独立以来,新生政权和本土社会结构之间具有某种“亲亲性”,使国家权力、资源的争夺与相应的社会结构对接起来,族群作为特殊的“文化与政治”单位被动员起来以争取并维护“共有”资源。因此大部分非洲国家曾经或正陷入族群政治冲突的旋涡,从使国家分崩离析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种族灭绝),到因选举而导致的暴力,因土地、水源和牧场等自然资源引发的冲突,等等。族群政治冲突已成为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根本性原因之一。虽然从理论上看,非洲国家的国内冲突不可能都是族群冲突,但由于很多冲突在动员和操控时往往都被打上“族群”的标签,赋予族性的意义,族群冲突毫无疑问是非洲最主要的暴力形式。有证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群体间冲突的暴力事件大幅增加。据米克尔·埃里克森(Mikael Eriksson)等人统计,1989~2002年,全世界共发生116 起主要的武装冲突,其中仅有7 起是传统的国家间冲突,其余109起几乎都是国内族群冲突,而非洲则是世界族群冲突的“主战场”。
非洲去殖民化以及殖民地大规模独立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主要武装冲突的总量逐渐增加;整个20世纪80年代,武装冲突再次强劲增长,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40%以上的国家都在经历冲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冷战期间非洲战争的顽固性和持久性,且该时期的战争很少通过谈判来解决;也是因为随着政治议程从“打天下”(建立独立国家政权)到“治天下”(设计和实施公共政策的细节),社会冲突自冷战时期后几年里猛增,最终在1991年达到顶峰,约占全球冲突总量的1/3。之后这一总体趋势发生逆转,到2004年,战争的总体规模降至峰值的一半左右。一些最严重和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结束,例如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安哥拉的战争等。
此外,该时期非洲冲突的区域性特点也极为明显,以下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四大区域的总体情况。
冷战结束后不久,中部非洲的武装冲突有所增加,1994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在这一区域,几乎所有武装冲突都是社会冲突,外部势力干预当地冲突或越境追剿叛乱集团是很常见的现象,冲突导致大量难民产生。刚果(金)的问题主要在于资源争夺引发的族群冲突,加上跨境族群的复杂性以及邻国难民蜂拥而入,导致该国长期政治动荡。
东部非洲地区长期存在严重的武装冲突,暴力程度也是所有非洲次区域中最高的,冷战后依然如此。这一地区由于冲突的复杂性、持久性和高度暴力性,可能更难解决和恢复。而且,当地普遍贫穷以及生态环境和社会系统长期崩坏,可能会使冲突进一步“雪上加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地区的难民人口数量尤其是国内流离失所之人非常多,为中部非洲的2倍。在90年代初达到峰值后,难民数量曾有所下降,但随着2003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爆发严重暴力冲突,这一数字再度大幅攀升。
在西部非洲地区,除尼日利亚外,很多国家的规模较小,人口不多,总体上暴力水平较低。然而,从1989年利比里亚内战开始,20世纪90年代西非地区的暴力水平升温和冲突事件数量急剧增加。自那时起,暴力活动蔓延至利比里亚周边地区。尼日利亚在帮助稳定该区域的安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它本身也面临重重困难,族群暴力肆掠。该地区冲突造成的破坏程度,虽然在某些地方相当严重,但较之中部和东部非洲地区相对较轻。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南部非洲的冲突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冷战期间,该区域经历了暴力程度极高的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白人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参与冷战各方力量的角逐和对抗。随着公开敌对行动的结束,大量难民重新定居或返回家园。此后尽管一些紧张局势仍然存在,分歧也很普遍,但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动机重新动用武装来解决这些争端。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死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The People’s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在安哥拉实现和解,这一地区的局势进一步趋稳。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的族群冲突虽依然是这块大陆的“主旋律”之一,但与以前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新趋势。
(一)武装冲突的死亡率正在下降
20世纪90年代,冲突致死人数最高的两个年份(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除外)分别为1990年和1999年,各死亡95067人和98805人。进入21世纪后,死亡人数有所下降,如2000年死亡67843人、2014年和2015年分别死亡67594人和67683人。死亡人数看似变化不大,但非洲人口已从2001年的8.36亿人增加到2017年的12亿人,这意味着死亡率已经降低。武装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从2001年(即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境战争结束)到2017年的这段时间,非洲因武装冲突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7个国家分别是苏丹、尼日利亚、刚果(金)、索马里、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利比亚。
(二)冲突及参与冲突的行动者越来越“碎片化”
非洲冲突及参与冲突的族群、宗教及政治派系的数目正在不断增加,这在苏丹达尔富尔等地区非常明显。例如,2011年5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所有达尔富尔利益攸关方会议”(All Darfur stakeholders Conference)最终敲定了和平进程,参与该会议的各种派系构成极为复杂。再如,中非共和国的反政府武装“塞雷卡联盟”(Seleka coalition)由5个独立的组织构成。马里北部的武装冲突中,图阿雷格人(Tuareg)与伊斯兰叛军本互为盟友,但在2013年1月法国军队重新夺回马里北部后的“塞尔瓦行动”(Operation Serval)中反目成仇。在刚果(金)东部省份,“刚果革命军”(Congolese Revolutionary Army)也分裂成不同的派系。
(三)武装冲突的跨国性突出
一些武装冲突具有很强的跨国性,武装分子能轻松跨越边境。不过这些组织很少能对政府构成重大军事威胁,或拥有能够占领和控制大片领土的军事力量。一些稳定性较好的国家,如马里、塞内加尔、乌干达,冲突通常发生在外围地区;另一些国家,如刚果(金)和苏丹(分裂前),则利用中央政权的孱弱进行博弈。
有很多国家存在跨境族群。以刚果(金)为例,在其西部地区,刚果人(Kongo)跨刚果(金)和刚果(布)两国而居;部分班巴塔人(Bambata)、巴荷洛人(Baholo)和乔奎人(Chokwe)则生活在安哥拉境内。在北部边境,有6个族群跨界刚果(金)和中非共和国,其中较大的族群有扎卡拉人(Nzakara)、阿班贾人(Abandja)和阿克雷人(Akare)。在东北部地区,阿巴卡人(Abaka)和卡夸人(Kakwa)跨境南苏丹。在东部地区,胡图人与图西人在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3国都有分布。在南部地区,隆达人、拜施人(Baushi)、巴拉巴人(Balamba)和巴贝巴人(Babemba)跨界刚果(金)和赞比亚。跨界族群的存在,既造成了地区局势混乱,又为周边国家干涉刚果(金)内政提供了借口。另外,族群冲突与组织犯罪网络及非法活动(包括洗钱、绑架、贩毒、恐怖主义等)之间有趋同的走势。在许多情况下,以前由外部资助的冲突,转而向内部寻求资源。冲突方利用钻石(安哥拉的安盟)、钶钽铁矿[刚果(金)东部各派]、咖啡和可可(科特迪瓦),甚至木炭(索马里)作为替代的收入来源。一般来说,这些“靠资源支撑的武装组织”无法发展成大规模的战斗力量,也缺乏挑战国家主要政党的力量。
(四)与选举直接相关的冲突充分释放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巨变,以及非洲各国内部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非洲实行一党制或军人统治的国家都遭受了西方“多党民主”浪潮的猛烈冲击。一时间,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几乎被视为医治非洲病症的“灵丹妙药”。西方政界和舆论界曾乐观地预测,整个20世纪90年代将是非洲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年代。那么结果如何呢?现实情况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世界上新实现民主化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非洲尤甚,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似乎陷入危机。这种情况在政府派系斗争活跃、个别族群利益凌驾于其他族群利益之上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伴随着不同程度暴力的选举在尼日利亚、肯尼亚、科特迪瓦和津巴布韦等国时有发生。例如,在津巴布韦2008年总统选举中,与选举有关的暴力事件导致200多人死亡,至少1万人受伤,数万人流离失所。又如,尼日利亚2011年选举后暴力事件在北方14个州,如卡杜纳、阿达马瓦、卡诺和包奇等州肆虐,其中以布哈里的家乡卡杜纳州最为激烈,根据警方数据,该州共有401人丧生,死亡人数在全国居首。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推动多党选举使非洲大部分地区相关暴力事件增加,这种趋势一直持续。
以肯尼亚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多党选举以来,共经历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2013年及2017年6次大选。大多数选举周期内爆发过程度不等的族群冲突,让世人产生“逢选必乱”的印象,而这些冲突也造成了极其致命的后果。
(五)资源冲突大幅增加
争夺诸如土地和水源等民生资源方面的局部暴力,其中包括常见的农牧民族群冲突也在增加,相关冲突存在于非洲许多国家的乡村地区。该类冲突的数量和样本极其庞大,从广度和数量上来说,构成了非洲族群冲突的类型之最。有证据表明,非洲基层社会的资源竞争相对容易产生暴力。据统计,2010年和2011年,资源性冲突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冲突的35%。而在欧洲、中东和马格里布,以及亚洲和大洋洲的所有冲突中,只有10%为资源冲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发布的报告《2030年全球趋势:替代的世界》指出,未来20年资源稀缺性可能会是地区性或国家性的,但不会是全球性的。该报告还认为,非洲和中东的脆弱国家最容易面临粮食和水资源短缺的风险。此外,包括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院(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在内的很多著名智库对于非洲“未来的资源战争”充满警惕。
以尼日利亚农牧民之间的冲突为例,在2012~2017年5年的时间里,尼日利亚至少发生了370起农牧民之间的冲突,而此前15年总共才有20起。2016年尼日利亚全国范围内的农牧民冲突导致约2500人死亡,2018年1月到6月爆发的冲突事件超过100起,至少1300人死亡,大约是“博科圣地”同期导致平民死亡人数的6倍。富拉尼人(Fulani)是尼日利亚游牧族群的主体,制造了与农民的绝大部分冲突。过去20年里,“富拉尼民兵组织”和农民之间的冲突已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仅2014年就有超过1200人丧生,这让“富拉尼民兵组织”成为当时世界第四大最极端的激进组织之一,仅排在“伊斯兰国”(ISIL)、“塔利班”(Taliban)和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之后,甚至还超过“博科圣地”(Boko haram)。以贝努埃州为例,2013年至2016年富拉尼人与当地农民发生的冲突每年都造成数百人死亡。
(六)族群与宗教冲突交织现象突出
类似苏丹分裂前南北族裔和宗教对立的社会形态,在乍得、尼日尔、马里、尼日利亚等国家都存在,只是不如苏丹那么严重。尼日利亚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则是族群与宗教冲突交织最典型的例子。当前大众媒体或学界一般将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引发的暴力事件描绘为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对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片面和偏颇的,因为其忽视了该组织行动中的族群因素与影响。在尼日利亚等国家,宗教身份与族裔身份在很多时候相互重叠,两种身份不断交织和强化。“博科圣地”的成员主要为北部的穆斯林卡努里人(Kanuri)和豪萨-富拉尼人(Hausa-Fulani)及科吉人(Kogi),他们对于南部的基督徒伊博人(Ibo)尤其仇视。2012年1月6日,“博科圣地”在阿达马瓦州共杀害18名伊博族人,随后大约22000名伊博人和约鲁巴人(Yoruba)逃离该州。2012年1月20日,卡诺市10余个场所发生爆炸,导致数百人伤亡,恐惧和绝望的情绪弥漫,来自南方的移民纷纷逃奔自己的家乡。同样,“博科圣地”在北部的所作所为,也引起居住在南方的豪萨-富拉尼等族群的恐慌,因为一旦大规模的族裔-宗教性质的冲突爆发,他们亦不能幸免,南部族群激进分子大有人在,随时准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比如,针对“博科圣地”的恐怖行为,伊博人的族群组织欧布尼歌维·尼伊博(Ogbunigwe Ndigbo)向所有居住在南方的豪萨-富拉尼等族群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两星期后离开,否则将有性命之忧。不能不说这种族群与宗教交织的状况是“博科圣地”“剿之不尽”的重要原因。
贫困率、民主化、政权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和邻国冲突的外溢等结构性驱动因素有助于解释非洲为何会频发族群冲突。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常常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洲未来的和平与稳定。
(一)高度贫困
目前大约37%的非洲人(4.7亿人)处于极端贫困中,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9美元。据预测,到2023年非洲处于赤贫的人口比例将减少约1%,但由于人口增长,赤贫人口的绝对人数则可能增加到约5.13亿人。非洲也不太可能在2030年之前实现联合国关于消除绝对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到这一年仍将有32%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虽比当前占比下降5个百分点,但绝对人口将高达5.35亿人。贫困率最高的国家是布隆迪、马达加斯加、刚果(金)、利比里亚、索马里、中非共和国、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南苏丹、几内亚比绍、尼日利亚和多哥,它们有50%以上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在非洲,理论上说较贫困国家比富裕国家更容易引发国内武装冲突,因而这些国家存在更大的族群冲突的风险。另外,由于族群冲突的破坏性影响,各国在安全方面的支出势必增加,对于贫困国家可谓“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
(二)民主化
民主化导致乱象丛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与成熟的民主国家相比,非洲国家往往出现选举输家不接受选举结果的情况,轻则质疑选举获胜方在选举中舞弊甚至操纵选举,重则引发选后冲突甚至内战。这是一种“输家政治”的现象,即选举输家不接受选举结果、不愿通过法律渠道质疑选举结果,或者虽然通过法律渠道但不接受法律裁决,相反采取从抵制直至冲突的对抗性措施。自非洲各国结束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以来,“输家政治”就长期困扰着非洲国家,成为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顽疾之一。据统计在1960~2012年,非洲各国共举行过335次总统选举,其中约有半数的选举失败方接受选举结果(167次,占49.85%),而对选举结果不满甚至不服进而采取各类抵制措施的多达121次(占36.11%),另有47次总统选举在当年便直接引发了暴力冲突、政变甚至内战(占14.02%)。由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波及非洲大部分国家,多党选举在这些国家成为一种避无可避的政治“必选项”,“输家政治”就长期困扰着非洲国家,成为非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顽疾之一。据统计在1960~2012年,非洲各国共举行过335次总统选举,其中约有半数的选举失败方接受选举结果(167次,占49.85%),而对选举结果不满甚至不服进而采取各类抵制措施的多达121次(占36.11%),另有47次总统选举在当年便直接引发了暴力冲突、政变甚至内战(占14.02%)。由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波及非洲大部分国家,多党选举在这些国家成为一种避无可避的政治“必选项”,“输家政治”现象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导致的暴力冲突也越发严重。
很多国家的选举往往是一种“赢家通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族群对国家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比例。一旦族群内部的权势集团不仅需要利用族众热情完成斗争目标,而且试图避免权力当局向中间市民让步之时,民主化便催生了族群意识。在部分民主化的条件下,精英经常能够通过它们对政府、经济和大众媒体的控制来宣扬族群意识,从而设置争论议题。精英努力说服人们接受其观念,族群冲突正是以这种副产品形式出现的。民主化很可能在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缺乏公民技巧和代议制发展落后及新闻专业主义制度的人口中、在精英感到被民主化变化所威胁的国家,触发族群冲突。
(三)政权类型的相关性
大多数非洲国家是混杂政体类型,在政治术语上称为“中间政体”(Anocracy)。这是结合了民主与威权两种特征的政体类型,属于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之间的灰色区间(过渡形态),类似于两不像政体(hybrid regime)、半民主政体(semi-democracy)或半威权政体(semi-dictatorship)。中间政体的政府部门和政治精英的基本功能及行动连贯性较差,往往具有不稳定性、效率低下等特征,容易遭受政治事件的牵连,比如武装冲突的爆发、领导层的意外变动(如军事政变)。中间政体国家既有专制因素,也有民主因素,会定期举行选举,但立法部门无法有效监督政府的行政部门。
有研究表明,中间政体的政局较之专制政体更不稳定,而后者的稳定性又显然远无法与成熟的民主政体相提并论。中间政体发生族群冲突的可能性是民主政体的6倍、是专制政体的2.5倍。一半以上的中间政体国家平均在5年内经历过重大政权更迭,在10年内经历政权更迭的概率高达70%。在一些中间政体国家,若某个族群独揽大权,尤其容易制造政局动荡。
(四)青年人口膨胀
青年人口膨胀(youth bulges)指的是在一国总的成人人口数量中,15~29岁人群基数特别庞大。膨胀的青年人口是冲突和高犯罪率的重要诱因,特别是在贫穷国家,青年人缺乏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政治发言权和参与权非常低,极易卷入暴力冲突事件或犯罪活动。不过与大规模的内战相比,青年人口膨胀似乎更多与低强度的冲突具有相关性。
非洲目前中位数年龄为19岁,年龄结构年轻化。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生育率,例如,在尼日尔、索马里、刚果(金)和马里等国,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6胎。除了吉布提、佛得角、博茨瓦纳、南非、埃及、利比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外,其他所有非洲国家都面临青年人口膨胀的结构性问题。预计到2023年,乌干达、乍得、尼日尔、索马里、马里、安哥拉、马拉维、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布基纳法索等国的青年人口膨胀尤其突出,该问题一旦与高失业率相勾连,将成为诱发族群冲突的重要原因。
(五)邻国冲突的外溢效应
当国家处于一个充满冲突的区域,容易受到冲突外溢的影响。刚果(金)是大湖地区各国族群冲突外溢效应最大的受害者。1994年大屠杀前的卢旺达由胡图人掌权,大量受迫害的图西人逃难到刚果(金),人数在1994年达到顶峰。此后图西族领导人保罗·卡加梅执掌卢旺达,一些胡图人及其武装又转而向刚果(金)撤离。1996年,属于图西人支系的班亚穆伦盖人(Banyamulenge)开展反蒙博托政府的武装行动。卢旺达军队以支持图西人的名义进入刚果(金),趁机打击胡图人反政府武装。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同样以这一名义支持图西人组建的反政府武装“刚果民主联盟”(Rally for Congolese Democracy)。在第一次刚果战争期间,乌、卢两国有超过6万人的部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图西人的军事夺权行动。
此后,卢、乌两国长期在刚果(金)保持存在,直到2012年兴起的“刚果革命军”,仍有证据显示卢、乌两国在为其提供暗中支援。周边国家对刚果(金)的干涉,有经济因素的驱动,但更多是出于维护本国安全的考虑。例如,卢旺达要打击游荡于刚果(金)东部的“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Democratic Forces for the Liberation of Rwanda),乌干达则要打击“圣灵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刚果(金)与安哥拉的关系上。20世纪70年代,安哥拉内战爆发,处于下风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以下简称“安盟”)向刚果(金)撤退。支持“安盟”的主体族群是奥温本杜人(Ovimbundu),而该族群在历史上与刚果(金)的跨界族群乔奎人保持了友好关系。“安盟”进入刚果(金)之后,得到了乔奎人的同情和支持,得以在刚果(金)生存下来。安哥拉政府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派兵参与第二次刚果战争,目的就是打击流窜于刚果(金)的“安盟”武装。
另根据《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坦桑尼亚是正在取得发展进步的国家,但由于邻国冲突而导致其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损失约0.7%。自2014年底布隆迪政治危机爆发以来,坦桑尼亚已经接收了25万名来自布隆迪的难民。坦桑尼亚还因与刚果(金)接壤而深受该国暴力冲突的影响。
以“族群名义”组织和动员的冲突是现代多族群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特别是冷战之后,类似的冲突席卷世界每个角落,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或暗潮涌动或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到东南亚绵绵不绝的群体对抗,再到非洲大陆此起彼伏的暴力和内战,无不弥漫着狭隘甚至血腥的族群/民族主义意识与情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下族群冲突超过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对抗,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只要国家或某个族群控制大量资源,就会持续面临族群政治的威胁。又或者,只要族群之间在关联和血统上有足够的区隔性,猜疑、恐惧、敌意与暴力便很难避免。人们不断地诉诸族群情感,希望借助它的力量解决自身的生存困境,若世人都做此想,所汇聚的力量该是如何磅礴,当这种愿望相互交错、相互竞争、相互抵制,残酷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而暴力的程度则视彼此的政治关系与利益互动而定,从漠不关心到剥削、轻视、压榨甚至屠杀,不一而足。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Isaacs)曾在20世纪70年代的断言,从当时的情况看,看不出有哪个族群不会重蹈覆辙。这依然是当今非洲族群冲突问题显著的真实写照。
©️本文版权归作者【先晓书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