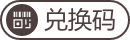-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神话美学与艺术丨变形神话
作者:姜金元
来源:《神话美学与艺术》
发布时间 2021-05-18 14:35 浏览量 1169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第一节 变形神话
变形是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基本主题。美国民俗学家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将“变形”定义为:“一个人、一个动物或物体改变了自身的形状并以另一种新的形状出现,我们称之为变形。”
神话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变形。在理性尚未发达的早期人类心目中,万物尚未获得固定的属性,事物可以自由地变换性状和功能。正如儿童的世界是变形的、幻化的世界。在儿童的眼中事物之间的区分尚未形成,事物之间的壁垒还没有建构起来。更重要的是,儿童能真诚地感受这种变形。
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的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姊姊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姊姊挂下一只篮来,宝姊姊坐在篮里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说“瞻瞻要上去,宝姊姊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见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相,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看看,哭哭,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作品插图
变形神话即讲述神祇、人、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事物发生形体变化的神话。神话世界处处都是变形,变形是神话的基本主题,变形神话构成神话的基本类型。
变形神话首先是记述神祇的变形。神话中的神之为神,乃因为其神通广大,而神通广大的表现之一就是其能幻化变形,主神宙斯常常变化自身的形态,如中国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
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看到小爱神丘比特正拿着弓箭玩,便不客气地警告丘比特说:“喂!弓箭是很危险的东西,小孩子不要随便拿来玩。”丘比特有两支箭,一支金箭,一支铅箭,被金箭射中的人,心中会立刻燃起恋爱的热情。被铅箭射中的人,则会十分厌恶爱情。丘比特为了报复阿波罗的歧视,就向阿波罗射出了点燃爱情之火的金箭,阿波罗心中立刻对爱情有了强烈的渴望。这时候,河神女儿达芙妮(Daphne)从旁边经过,丘比特将铅箭射向达芙妮,达芙妮立刻变得十分厌恶爱情。被爱情之箭射中的阿波罗深深地爱上了达芙妮,对她表示爱慕。达芙妮厌恶地说道:“走开!我讨厌爱情!离我远一点儿!”说着便逃进山谷。阿波罗穷追不舍,并拿出竖琴,弹出优美的曲子。达芙妮听到了这优美的琴声,被琴声迷住了,不由自主地循声而来。躲在石头后面弹琴的阿波罗立刻跳出来,要拥抱达芙妮。达芙妮见状拔腿就跑,阿波罗则在后面苦苦追赶,眼看阿波罗就要追上了,达芙妮急得大叫:“救命啊!”河神听见了达芙妮的求救声,立刻用神力把她变成一棵月桂树,达芙妮的秀发变成了树叶,手腕变成了树枝,两条腿变成了树干,两只脚和脚趾变成了树根。意大利的雕刻家乔凡尼·洛伦佐·贝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1598-1680)的雕塑《阿波罗和达芙妮》展示了达芙妮变形的瞬间。

《阿波罗和达芙妮》
神话变形是隐喻性的,具有多种文化意义。以达芙妮化为月桂树为例,维柯认为阿波罗的追求是神的行动,他是个文明之神,试图教导和感染达芙妮,而达芙妮的逃跑是动物行为,因为她代表了原始时期在荒原中流浪的妇女。而她变成树的寓意则是人类因为神的训导开始了定居和财产的需求,并誓死保卫自己的领地。而这种私人的领地也成为家族父主们的埋葬场所,这种埋葬死者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安慰自己家族的灵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维柯认识到,宗教、婚礼与葬礼是所有异教民族都必然遵循的三种习俗,这三种习俗是人类三个头等重要的原则,正是在这三种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人类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社会文化和典章制度。
变形神话的另一形式是人与物之间的互换变形。
我们先看由动物变成人形。北美印第安苏族人认为动物与人之间可以变形转换。在他们的神话中记录了大量此类变形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一点光明,太阳和月亮被一位住在山顶的老人藏在家里,乌鸦听到人们的抱怨,就想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于是乌鸦趁老人的女儿喝水之际,变成一片细小的松针进入姑娘的肚子,幻化成了人形。十个月后,姑娘生出了一个白胖的男孩。一天晚上,老人和女儿都睡着了,男孩带着月亮和太阳从烟囱爬了出来,老人发现后,紧追不舍,孩子一路狂奔,跟头连连,最后把太阳、月亮抛上天空,现出原形飞走了。”“年轻女子的爱犬变成人形,同女子交合,后来女子生下了五只小狗,经过一番周折,五只小狗都变成了人,他们长大后因为带着神灵的力量和狗的素质,成为部落中很好的武士。”
与动物变成人形相反,人也可变成动物。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记载了大量的人变形为动物的神话故事。黑格尔透过这些故事发现其中隐含的价值判断——贬低动物性的东西,与对动物的崇拜相反。“从精神的伦理方面来看,变形对自然是抱否定态度的,他们把动物和其他无机物看成由人沦落而成的形象。”因在价值的阶梯上动物低于人,人变成动物一般都是被动的,是惩戒性的。如安徒生童话《野天鹅》中11位王子被恶毒的继母实施魔法变成了野天鹅。
不过在早期神话中人变成动物或者植物,并非都是被动的。中国神话典籍《山海经》中有大量这类的变形故事,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列子·汤问》亦载:夸父追逐日影,追到隅谷,口渴难耐,将黄河渭水的水都喝完了还不解渴,将奔向北方大泽取水。未至,半道上干渴而死。弃其手中的武器,被尸体的肉和油浸渍过的地方长出一大片桃林。这种变形给人的不是悲惨的印象,而是悲壮的感觉,他是为追逐自己的梦想而死。
与后世作为惩罚手段或异化结果的变形不同,神话中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变形往往是基于生命一体化的关联,基于世界万物之间的统一性。在原始神话中,人的主体性意识尚未独立,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事物之间尚未因其特殊的规定性而分隔开来,事物之间可随意转化、变形。在空间和时间上,万物生命休戚相关,构成不能打破的统一性,这就是神话的基本原理。卡西尔描述神话的世界说:“对神话和宗教的感觉而言,自然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一个生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还未被赋予一种突出的地位。人和动物,动物和植物,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神话思维使那些在现代人看来彼此不相干的事物结合起来,融汇成一个无差异形态。在神话世界中万物互联互通,转化变形成为常态。卡西尔指出神话的真正基质不是思维而是情感,神话是情感的产物。原始人的情感趋向使得他的所有创造活动都染上了情感的色彩,他们信仰“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
神话世界混沌初开,万物尚未固化定型,宇宙肇始,品物流形。
原始先民信仰万物有灵,在他们看来,不仅人有灵魂,日、月、山、河、树、木、花、鸟等无不具有生命和灵魂。而且,基于灵魂和生命的一体化,万物是彼此相通、相互转化的。泰勒认为灵魂能够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或动物体内支配它们,甚至能进入在我们看来是无生命的物体内,影响它们。原始人相信人死后可以变成种种自然物。在万物互联的神话世界,任何事物之间都可以转换、变形,包括人与神(鬼)、人与动物、人与非生命物质、某物与另一物之间,诸如此类。《大荒西经》记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蛇、鱼、人相互转化、相互组合,而且能死而复苏。
变形神话就变形的方式而言有化生性变形,有组合性变形。化生变形神话是比较原始的神话,它以“生命一体化”为基础。中国神话中的女娃溺亡化为精卫鸟、夸父弃其杖化为桃林等便属于化生性变形。
化生性变形有一种特殊主题——宇宙化生。“在许多宇宙起源说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为:世界即宇宙人体;这样一来,宇宙的各个局部则与人体各个部位相应,堪称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两者同一的显示。”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杀死巨灵伊米尔,用伊米尔的尸体作为创造世界万物的材料,重建天地:以其肉造出大地,以其血造出海洋,以其骨骼造山岳,以其发造树木、花草,以其头颅造天宇,以其脑浆造云朵……阿兹特克人的神话中,诸神将地神之体分解为两部分,一半造天,一半造地,头发成为树木、花草,口、目成为河流、洞穴,两肩和鼻成为山岳和谷地。印度《梨俱吠陀》中记载:原始巨人布路沙的尸体化生为世界:由其头脑,产生月亮;由其眼睛,产生太阳;由其嘴巴,产生雷雨和火;由其呼吸,产生天风。由其肚脐,产生大气;头首为天,双足为地;由其两耳,产生四方,诸神制作,世界以成。中国神话中的盘古龙首蛇身,盘古临近死亡身体化为天地万物:“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绎史》卷一引徐整《五运历年记》)世界是拟人灵体所化,所以世界是神圣的。
组合性变形是变形神话的另一种变形方式。原始人类以感觉和情绪为基础,以想象为动力进行创造,把分离的和异质的事物或要素结合起来,创造出神奇的世界。
组合性变形在作为中华文化象征的龙的形象上体现得较为充分。龙是由多种动物拼合而成的神物。宋代罗愿在《尔雅翼》卷二十八《释鱼》中引用王符的说法,以为龙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麟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组合性变形反映了原始初民万物相连、人神相杂的世界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早期的人类在“绝地天通”之前,人神混杂。中国远古东夷族流行巫术,人神杂糅,人和神时时沟通。《国语·楚语下》记载,少皞为东夷首领,以玄鸟(凤凰)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其时人神相杂,自由交流。只是到了颛顼的时候,人间与神界的顺畅交流被阻断了,只有巫师才能交接神灵。
中国著名神话学家顾颉刚认为这种人神杂糅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人与神混杂。“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人与神混的,如后土原是地神,却也是共工氏之子。”其二,人与兽混杂。“人与兽混的,如夔本是九鼎上的罔两,又是做乐正的官;饕餮本是鼎上图案画中的兽,又是缙云氏的不才子。”神话传说中的“禹”原本也是一种动物,流传到后来,成了人王。禹是一条虫,从理性思维的角度看固然可疑,但在神话的世界里,这是真实的。古时称南方民族为“闽”,为“蛮”,保存人与虫混杂的痕迹,而《随巢子》中禹化为熊,《吴越春秋》中禹娶九尾白狐的故事,也可视为人兽混杂的印记。其三,神与兽混杂。鲧化为黄熊即为神兽混杂。
人神混杂体现在神话形象塑造上就是组合神的形象。希腊神话以人为中心,人形的神像占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神话典籍《山海经》中记录的神的形象以自然神为主,南方民族的图腾物凤凰是以鸡为外形的神物。《山海经·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凤有五彩灿烂的外观,它的出现象征着安宁、吉祥。
神的形象以兽形、人兽组合型为主。中国的创世神伏羲、女娲的形象都是人首蛇身。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凶神相柳也是人面蛇身。“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山海经·海外北经》)也有人面鸟身的神:“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禺强)。”(《山海经·大荒北经》)

敦煌藏经洞伏羲、女娲绢画
蛇在远古是灵物,《山海经》中记载有巫师“珥蛇”“把蛇”的形象。“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

夸父逐日
借助化生、组合等变形方式,神话创造出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形象。《山海经》中记录了大量的此类形象,“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鲁迅《阿长与〈山海经〉》)在古埃及神话中,有丰富的人兽组合形象:战争女神塞赫麦特(Sechmet)长着狮子的头和女人的身躯,死亡之神阿努比斯(Anubis)是长着胡狼头的男子,智慧神托特(Thot)则是长着鹮头的男人。神话世界的诸多形象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其客观对应形式,只能在想象的世界存在。
神话变形的产物就是各种神话形象。“形象乃是不容许再进一步的变形,它也只在转化完成后,才真正的展示出来。”后世看到的诸多神话形象只不过是神话时代流动的、绵延的世界的某些固化形态,有如暗流涌动的深渊中飞溅的几朵水花。“在那时期,变形被认为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天赋,并且持续演化下去。通常那个时候的世界被视为是流变的,不只是人可以使自己变形成任何东西,而且他也有力量可以变化其他东西。在宇宙的流变中,某些形象特别凸显,那些特殊的变态形象被固定成永恒的。人类所执着的形象,乃成为创造生命的传统,一直被传述下来;而那并非任何动物的抽象物,不是袋鼠或鸵鸟,而是袋鼠也是人,或者是人而可以自由地变成一只鸵鸟。”
原始人类为何要创造出怪诞的变形神话呢?变形神话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
希腊神话中的变形大多是策略式的变形,众神基于某种现实需要和策略的考虑,不希望让人看到他们的身影,便通过变形来隐身,也就是说,神之所以变形,是为了迷惑世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叙述特洛伊之战,诸神分别支持他们所属的战队,不过他们并非以自身的形象出现,而是幻化变形为动物和人。宙斯亲近阿喀琉斯,当阿喀琉斯受到委屈时,宙斯托梦给阿伽门农传递错误的信息,梦则幻化为阿伽门农最器重的顾问奈柳斯的儿子奈斯特的模样前去游说。而宙斯的弟弟海神波塞冬支持阿果斯人,他一会儿变成秃鹫,一会儿变成人形,到阿果斯人中间去给他们打气,出谋划策。特洛伊战争双方的交战处处有神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是诸神之间的较量、争斗,诸神以变换形象的方式参与到战争中去。
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奥德修斯返乡的途中充满艰辛,若不是智慧之神雅典娜的一路关照,奥德修斯早已葬身大海,而雅典娜帮助奥德修斯也是借助变形幻化。当奥德修斯回到陌生的故乡伊萨卡时,雅典娜再次出现,她先是变形为一个青年牧人,又变形为一个修长、美丽、典雅的女子。此时,已判明真相的奥德修斯佯装不知眼前的一切(回到了故乡,眼前的雅典娜),雅典娜终于揭开伪装,说“因此我的执拗的朋友,大骗子,心里总是在想阴谋诡计,甚至在他自己的故乡……我们两个都善于诈骗。在人世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你的深谋诡辩,而我的聪明才智是超乎众神之上的”。智慧女神的智慧似乎就体现在善于伪装变形,所以,奥德修斯对雅典娜说道,“女神,一个人无论多么有见识,很难一眼就认得你,因为你总是以各种形象出现”。为了帮助奥德修斯惩治趁他外出而骗吃骗喝的众多求婚者,雅典娜决定将奥德修斯的形貌加以改变:“我要改变你的形貌,使得人们不认得你。我将枯萎你那柔软肢体的滑润皮肤,去掉你头上的棕发;我将给你一身褴褛衣服,使人望而生厌;我将使你那双美好的眼睛黯然无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要使那班求婚者,甚至你留在家里的妻和子,把你当作一个肮脏的流浪汉。”
神不同于人的地方在于他具有超凡的能力,神像一个魔术师,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在不同的场合显示不同的形象。宙斯把美丽的少女伊俄变形为雪白的母牛,以逃脱善妒的妻子赫拉的伤害。宙斯到人间视察,人们不愿意接待他,唯有一对贫寒的老夫妇费雷蒙和鲍西斯收留了宙斯和他的儿子。于是,宙斯将老夫妇的破屋变为金灿灿的神庙,把冷酷心肠的人们的居住之地变成了大海。宙斯还满足老夫妇两人的愿望,在他们死后,把丈夫变成了橡树,把妻子变成了菩提树。神这位魔术师能按照某种意图显示出不同的形象来。
在变形神话中有一类变形是与逃逸相关联的。在神话和民间故事中有大量为了逃避追捕或追杀而发生的变形。奥维德的《变形记》中记载:雅典公主普洛克涅(Procne)与色雷斯国王忒瑞俄斯(Tereus)结婚5年,因为想念妹妹菲洛墨拉(Philomela),她请求丈夫将她妹妹从雅典带到色雷斯。忒瑞俄斯看见菲洛墨拉之后垂涎于她的美色,将她软禁在密林深处,谎称普洛克涅已死,诱奸了菲洛墨拉并要求她不要声张。菲洛墨拉知道真相后发誓要将忒瑞俄斯的丑行公之于众,恼怒的忒瑞俄斯残忍地割掉了菲洛墨拉的舌头,并将她遗弃。无法说话的菲洛墨拉在雪白的麻纱布上织出了紫铜色的字样,将自己的悲惨遭遇描绘出来,以手势哀求仆人将其送给王后普洛克涅。普洛克涅摊开麻布,知道了丈夫的龌龊与残暴,决意报复。她杀了儿子,用其尸体做成大餐让丈夫忒瑞俄斯吃下。忒瑞俄斯意识到二人的报复诡计之后,抄起武器便要追杀姐妹二人。眼看这对姐妹就要被追上,绝望之际她们向诸神祈祷让自己变形以逃脱忒瑞俄斯的追杀。诸神将普洛克涅变成燕子,菲洛墨拉变成夜莺,使她们逃脱了忒瑞俄斯的魔掌。
英国作家伊利亚斯·卡内提指出,“为了逃逸而转化(变形),亦即为了逃避敌人而转化,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事,世界各地的神话和神怪故事,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子”。卡内提将逃跑变形分为两类:直线型和循环型。所谓“直线型”是指一物追逐另一物,两者距离缩小,就在猎物要被逮住的一刹那,它发生变形成为另一种东西逃脱了。于是追逐会继续下去,或者更准确地说会重新开始。《西游记》中二郎神与孙悟空斗法,两者均通过变换法逃避对方的追捕。直线型变形的例子,卡内提列举了澳大利亚罗利亚族(Loritja)的神话:图腾祖先特库梯塔士(Tukutitas)以人的形象从地下冒出,悠游地生活,有一天,遭到一只巨型恶犬的追杀,他们拼命奔跑,唯恐速度不够快。为了弥补速度上的不足,他们分别变形为其他各种生物——袋鼠、鸸鹋、山鹰等。不过他们当中的每一位只能变成某一种动物,并且只要还在逃亡中,就要保持这种形象。
《奥德赛》记载:睿智的“海洋老人”普罗透斯是海豹的主人,每天他会和他的海豹们到沙滩上来一次。海豹先到,然后是普罗透斯。他仔细清点他的海豹群,然后躺在它们当中睡觉。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返回故乡途中遇逆风,漂泊到普罗透斯居住地附近,在此被困数年,墨涅拉俄斯和他的同伴们仍然寸步难行,他非常绝望。普罗透斯的女儿埃多泰娅(Eidothea)同情墨涅拉俄斯一行,给墨涅拉俄斯出主意,指导他如何做才能捉住她的父亲——那个能占卜未来的人,并迫使他说出答案。她给墨涅拉俄斯和他的两个同伴提供海豹皮,并在沙滩上掘洞让他们三人钻进去,然后盖上海豹皮。三人忍着恶臭,耐心地等候,当海豹群爬上沙滩,他们便混迹于海豹群中。这时,普罗透斯从海里冒出,清点他的海豹,然后安心地躺在它们当中睡觉。墨涅拉俄斯和他的两个同伴趁机将睡梦中的海洋老人捉住,死死不放。普罗透斯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挣脱他们,他不断变形,先变成一头长毛林立的狮子,然后变成一条蛇,但他们还是牢牢地控制住了他。他又变成一头豹子,然后又变成一头公猪,但他们还是紧紧地抓住他不放。他又变成水,变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他们还是不松手。在经历种种变形都无法挣脱束缚之后,普罗透斯终于缴械投降,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形象,回答了墨涅拉俄斯的问题。卡内提认为这是典型的循环型变形,每一次变形都在同一点上发生,并且每一次变形都是变成另一种形态,力图从另一个方面去突破,但最终又都徒劳无功。
这类逃逸变形隐含着人们试图突破自身限制的期待。从更广泛的立场上讲,神话变形更深沉的情感动因在于对生命有限性的突破。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山海经·北山经》)
我们略去其中的地理叙述——“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和“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这是一个经典的神话。关于这则神话的意义,后世多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加以理解,人们大多关注的是精卫“填海”这一征服自然的举动,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将精卫和刑天并置,突出其意志力。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中认为,精卫与刑天是属于同型的神话,都是描写象征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意志的,都是属于道德意识的神话。袁珂先生也认为,精卫填海表现了遭受自然灾害的原始人类征服自然的渴望,以及其身上体现的坚定意志。从人们的理智上看来,填海工作当然是徒劳的,但从感情上看来,沧海固然浩大,然而小鸟坚韧不拔地想要填平沧海的气概却比沧海还要浩大,此其所以为悲壮,为值得赞美。有的则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历史印记和文化象征意味,段玉明认为“精卫”即太阳鸟“金乌”,精卫填海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太阳沉没的神话,其背后铭记的是商代覆灭的历史,并欲借此激发一种复国情绪。
如果我们尽力还原原始先民的神话世界,这则神话蕴含着初民的灵魂观和超越死亡的意愿。
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灵魂是不死的。灵魂不灭的观念的产生基于两类现象。其一,当灵魂抛弃肉体,肉体便失去了生命力,就会产生疾病、死亡等;另外,原始人在睡梦等现象中发现灵魂可以暂时离开肉体而独立活动。在柏拉图的灵魂观中还遗留着初民的灵魂思想:“灵魂在取得人的形式之前,就早已离开人的身体而存在了,并且还是具有知识的。”灵魂在尚未堕入肉体之前,就已存在。“—个人未形成前大约就诞生了灵魂。这灵魂在天地间沉浮漫游,选择它所喜欢的女人作为自己萌芽的温床。”直至当代,依然有理论家认为死亡只是身体的消失,而灵魂不会消失,灵魂作为构成万物(包括人类)的基本粒子或能量,在人体消亡后会以另一种方式(如量子信息的方式)存活在世界上。“宇宙确实有超越的能量渊源……这个能量是生成万物的能量。神秘主义崇拜的就是这个能量。”在原始初民那里,这个能量是弥漫宇宙的不朽的灵魂,正如庄子笔下的“气”,“通天下一气”,万物都是气的不同形态的呈现形式,人的生死也只是气两种形态,“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表达了宇宙间的“常”与“变”,灵魂是常在(时间上永恒而空间上遍在),只是变换了居所:“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但没有消亡。灵魂来来去去/居住于它想居住的地方,变换着居所,/从兽到人,从人到兽,但它/总是存在着。就好像融化的蜡/被新的印章盖上,尽管蜡的形状变化了,/不再是以前的形状,但是/它仍然是蜡,所以我说灵魂/始终不变,/尽管身体外形一直在变。”
灵魂可以依附于肉体而存在,也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在原始人的世界里,人的肉体可以死亡,而灵魂生生不灭,并猜想:在可见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鬼魂。神话思考世界最早都与死亡和坟墓有关。
中国有“女尸化草”的神话。
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 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山海经·中山经》)
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山海经·中山经》)
这个故事讲的是华夏始祖炎帝女儿的神话。《帝王世纪》记载,远古时代有一个国王,名字叫少典,他的妃子叫女登,女登到华阳游玩时,在一条神龙的感应之下怀孕,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炎帝。炎帝牛头人身,是火师、火神(太阳神)。他发明了农业,被尊为神农。他还尝百草发现各种草药,是中国的药神。炎帝有个女儿,名叫女尸,正值貌美青春,尚未出嫁便死去了,死后变成一种美丽的 草,它的叶子层层相叠,它的花黄得晃眼,它的果实像菟丝子。这种草有神奇的魔力,谁吃了它就能让别人爱上自己,就如同丘比特的金箭。这是山鬼、巫山神女的原型。
草,它的叶子层层相叠,它的花黄得晃眼,它的果实像菟丝子。这种草有神奇的魔力,谁吃了它就能让别人爱上自己,就如同丘比特的金箭。这是山鬼、巫山神女的原型。
在早期神话中,女尸化草隐含的是生命与死亡的纠葛。古人从春草年年绿、桃花年年开等自然现象中感受到循环的时间和生命的轮回和永恒,故女尸化草正是神话世界中生命不死的印记。《抱朴子·仙药》云:“芝赤饵之一年,老者还少。”即表明 草(灵芝、芝赤)具有起死回生、延年益寿的功能。不论是女尸变形为
草(灵芝、芝赤)具有起死回生、延年益寿的功能。不论是女尸变形为 草,还是女娃变化为精卫鸟,都以美好的形态延续生命,对抗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而变形是超越有限生命的表现。《述异记》记载:“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状如海燕。”女娃变形为精卫,精卫又生育后代,生生不息。
草,还是女娃变化为精卫鸟,都以美好的形态延续生命,对抗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而变形是超越有限生命的表现。《述异记》记载:“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状如海燕。”女娃变形为精卫,精卫又生育后代,生生不息。
原始初民相信生命是可无限延续的,永恒的观念在原始人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死亡”的观念是在后来才不得不接受的。在原始初民那里,借助共有的灵,一物可以转换成另一物,这就是变形神话的内在机制。“它(灵魂)能够离开肉体并从一个地方迅速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它能够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中去,能够进入动物体内甚至物体内,支配它们,影响它们。”卡西尔认为,“神话教导人们死亡并非生命的结束,它仅意味生命形式的改变,存在的一种形式变成了另一种形式,如此而已,生命与死亡之间,并无明确而严格的区分,两者的分界线暧昧而含糊,生与死两个词语甚至可以互相替代”。
在原始人类那里,变形并不是一种手法,而是一种精神性的概念,一种信仰。在原始先民看来,万物是互通互联的生命体,不同的事物可以相互转化,变形成为神话世界万物显现的基本形态。正如恩斯特·卡西尔在比较神话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区别时所言。
当科学思维想要描述和说明实在时,它一定要使用它的一般方法——分类和系统化的方法。生命被划分为各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彼此是清楚地相区别的。在植物、动物、人的领域之间的界限,在种、科、属之间的区别,都是十分重要不能消除的。但是原始人却对这一切都置之不顾。他们的生命观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生命没有被划分为类和亚类;它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各不同领域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栅栏,而是流动不定的。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形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性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
变形也是神话对后世特别是艺术家产生吸引力的地方。神话的本质是变形,神话的魅力也在于其变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利亚斯·卡内提一生从未终止过对神话的阅读,直到晚年他自问:究竟是什么让你对神话如此着迷?答案是“变形”。卡内提甚至将变形视为人的本质。“人是变形的动物,因为具备变形的本领,才变成了人。”原始人类将这种变形的本领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神话变形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变形作为一种手法或技艺在后世的艺术生产领域得到了集中体现。变形是艺术生产的基本规律,变形就是指作品中出现的艺术形象改变了对象原形的自然形态。所以,广义的变形是指艺术生产过程中对事物的形态加以改变的一种艺术手法。鲁枢元认为,“所谓变形,即文学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客观事物或社会现象的固有形态作出有意或无意的改变”。
神话变形不单单是一种技法,它同时是一种世界观,变形意味着生命形态的诸多可能性。变形也意味着生命的完善。神话变形与现代艺术中技术手法的变形的区别在于,它不单是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它首先是神明或神性的显现。其变形的动力不是人的虚构、想象,而是宇宙深处的奥秘。
随着机械时代的来临,社会角色的固化,人的变形能力渐渐流失。在现代分工以及“专业化”(Spezialistentum)的规制下,生命的空间变得越来越逼仄。卡内提曾哀叹,现代社会人类原有的“变形”能力逐渐消亡。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被动的、异化的变形,如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为甲虫。变形演化为一种负面的形象。面对强大的客体化世界和固化的生命形态,卡内提寄希望于艺术家,他把作家封为“变形的守护者”。
借助变形,人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诸多可能性,实现生命的升腾。默里·斯坦因在《变形:自性的显现》中对变形解释道:变形是对自我的一种完善,每次变化都朝向那个最理想的目标,都是一种进步,虽然每一次都存在欠缺。“变形中的人并不必然是引起我们的羡慕和唤起仿效的理想的人。他们是处在变形过程中的,因而常常是有欠缺的。他们在变成他们自己,而奇妙的是他们也在变成他们还不是的东西。”
©️本文版权归作者【先晓书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