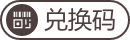-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对“志愿”理解的中西之差
作者:罗婧
来源:仁爱遇上效率:中国语境下的志愿过程
发布时间 2021-06-07 10:42 浏览量 203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
导论 “土特产”,还是“舶来品”?
“志愿”(volunteering)是近代以后才在国际上流行开来的概念,不过,其包含的以仁爱(benevolence)为基底的思想、倡导的互助行动却早已存在。这在不同的时代、社会、文化中都有迹可循。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仁爱、乐善、慈悲等是儒、释、道等学说共同推崇的,不论是君王还是平民,社会成员的施善、行义等事迹被广为传颂。这样来看,若是抛开概念的外壳,“志愿”并非西方的发明。“志愿”在我国也就不能被笼统地归结为舶来品。
但不可否认,传统的仁爱、善行等与当今的志愿在“名”“实”上皆有差异。志愿不仅强调仁爱、慈善、奉献等,还十分强调对效率的追求。这与志愿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中的发源脱不开干系。伴随着西方近代早期以来福利思想的多样化,各类志愿组织应运而生。这些志愿组织试图从世俗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角度来应对多元的福利需求,从补充(supplementary)、互补(complementary)的角色,成长为与国家、市场并驾齐驱的理念内核和运行机制。志愿主义的支持者提出,在福利提供上志愿部门比国家和市场更有效率。因为其具备重建社会道德的功能,能够促使社会运转,形成良性循环,从根本上增进福利。可见,效率是福利提供主体的合法性来源,是其能否在福利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根本。
自近代以来,以西方社会为土壤的志愿思潮广泛传播,流入我国,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慈善精神、互助活动等的发展走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以志愿为名的事业生长而出。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志愿服务事业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与支持,蓬勃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前,志愿的理念蕴藏在各类义务运动中,比如爱国卫生运动、学雷锋运动、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等。这些义务运动将爱国、服务人民、团结、友爱等结合起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平台。改革开放后,志愿服务事业作为动员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覆盖了教育、文化、环保、扶贫、救灾等多个领域。志愿者、志愿组织等既进行了因地制宜的尝试和创新,又不断吸收国外经验,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提升服务的效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志愿服务事业更是飞速发展。到2018年,我国志愿者总数约为1.98亿人,志愿者组织总量达到143.30万个,它们对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可见,不论中西,志愿的扎根、成长本质上都是在力图兼顾对仁爱的传承和对效率的追求。当然,基于中西社会基础、文化机理的不同,传统的仁爱的内涵不同,仁爱与效率的相遇也呈现不同的张力。这进而形塑了中西志愿各自的形态,以及志愿者、志愿组织、志愿服务领域等在各自福利格局、治理体系中的角色。
以英国为例,西方社会中仁爱理念的转型和作为一种福利理想的志愿主义的产生,是以批判国家、教会的福利实践为基础的。一方面,从14世纪起,英国教会内贪污腐败的现象十分严重,教会慈善成了神职人员敛财的途径,这使教会失去了捐赠者的信任;另一方面,17世纪颁布的《济贫法》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让贫困者“既安于现状又自甘堕落”,并且很多穷人不愿意接受救济,认为这是耻辱的、遭鄙视的。从而,志愿的、世俗的、具有福利功能的组织大量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西方志愿部门,本就怀有替代国家、教会去提供福利的初衷。它们认为传统教会、国家的仁爱理念是父爱主义的,在对此展开批判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福利实践途径,力图避免“制造穷人”的后果。不过,志愿组织的尝试并非另起炉灶,其在理念上没有脱离宗教慈善的思想和传统的互助习惯,在实践上也并未完全与教会和国家割裂开来。有学者就认为,志愿组织对仁爱理念的重塑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新父爱主义”。可见,学者、实践者、政治家等基于自身的理解和立场,围绕究竟谁的理念更符合启蒙后的新道德、谁来提供福利更有效展开了辩论。这些辩论也推动了各个福利提供主体进一步在理念和实践上重塑、理顺了仁爱和效率,进而各自都建构出一套以自身为中心的福利理想模式。于是,在18、19世纪的英国,多元的福利提供主体争相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福利事业,在显露出各自优势的同时,也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失灵问题。这使得各个志愿部门意识到,单一主体之间需要合作和协同。“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志愿失灵”等理论就以不同的主体为中心,寻求不同主体“分而治之”——在福利提供、社会治理中进行分工合作的方法。由此,围绕如何理解各福利提供主体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不同的“措辞”,比如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激进主义等。由此可见,西方语境中的志愿服务事业不仅是福利工具和治理手段,还是自成体系的理念和思想。其对仁爱和效率的建构与国家、市场等其他福利提供主体是区别开来的。
但中国则不同。在传统社会中,各个福利提供主体,比如宗族、朝廷、寺庙、明末出现的善堂善会等在解读包含仁爱在内的一系列福利思想时融合了各家学说,形成了共享、相融的理念。这使得,在近代和当代的福利体系转型中,各个福利提供主体在对仁爱等福利思想的重塑和解读上也就有着相同的基础。所以,在志愿这一概念得以引入后,其虽然用来指代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之外的福利提供者,具有区别于其他福利提供主体的知识和机制,但其并没有独立地去构建对仁爱和效率的理解,而是在与其他主体的相互影响下着力塑造共同的认知,将福利的目标、思路、功能整合在一起。所以在我国,志愿组织是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之一。尤其是单位制社会转型后,志愿服务事业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还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成为满足社会成员多元需求的福利提供渠道和促进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平台。也就是说,我国并不存在以提供方来划分的,对于走什么样的福利道路的争议和分歧。这也就是为何西方的志愿研究通常绑定讨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中国是分割开来的。因而,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的志愿服务事业于整个国家福利格局、治理体系而言,不是具有替代性理念的对立体系或合作伙伴,而是纳入其中的、参与福利提供和社会治理的、促进社会整合的治理技术。
通过这些简明的回顾和比较可以看出,中西的志愿服务事业既有共通之处,也有本质的差别。一言以蔽之,中西志愿的理念和实践都是在理顺、调和、建构仁爱和效率中不断发展的。但仁爱的内涵不同,与效率碰撞出各异的火花,这使得中西的志愿服务事业在根系、表征上皆有各自的特点。当然,不论是西方自成体系的志愿,还是在我国作为技术手段的志愿,在建构福利思想的进程中需要理顺的不单是仁爱和效率,还有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一系列逻辑变化。本书在开头以仁爱和效率的相遇为线索,实际上是以仁爱来折射不同时代、文化下的社会理想,而追求效率则是近代以来关于如何实现社会理想中最广为人们接受的原则。两者是有关志愿的理念和实践得以萌生、发展的背景中,林林总总的变迁的缩影。透过两者相遇的线索,我们得以厘清志愿服务事业在中国有哪些普遍性和特殊性。
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既不是“土特产”,也不是“舶来品”,而是在本土和国际的双重影响下不断推进的。所以在发展中,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也遇到了很多与其他社会类似的发展困境。尤其是当其在试图寻找高效的通往仁爱之路时,势必要面对在转型中张力愈益凸显的利他与利己、自愿与义务等一系列理念的冲突。这就导致志愿服务事业在定义服务的专业性、探讨自身的可持续性等发展议题时遇到诸多的迷思。可在当前,我国志愿服务事业日益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治理职责,那么被寄予厚望的志愿服务能否卓有成效地承担起这些重任,就成为最紧要的研究问题。
在研究和应对这一问题时,以往的思路倾向于套用国外的理论进行分析,凭借其他社会的经验提供解决方案。但我国志愿服务事业有着自己的发展脉络,其遇到的发展问题与西方志愿服务事业的情况形同质异。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西方,各个福利提供主体之间的合作是在福利道路上搁置争议、寻求共识的“和解”和协同;而在中国,各个福利提供主体之间是基于相同目标和理念的共建共治共享。所以在分析志愿服务事业能否奏效、为何失灵时,西方的理论倾向于将根源归结到各个福利提供主体的关系上。但这样的分析显然难以套用到我国的情况中。比如,有学者借鉴西方的研究,使用了萨拉蒙的“志愿失灵说”来分析我国志愿服务工作在开展活动、发挥作用时遇到的问题,他们很快发现,我国所遭遇的“志愿失灵”与“志愿失灵说”中的“失灵”意涵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志愿失灵说”是在将福利提供主体相互分割甚至对立的社会基础上提出的,其所提供的解读、对策与我国的语境不相契合。所以,在分析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现有的实践困境和发展障碍、探讨其能否承担重任时,首先要回归到我国自身的语境中,定位志愿服务事业有哪些使命和任务。
全面、历史地来看,当前我国的志愿服务有三项重任,即参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参与社会治理和促进社会健康转型。首先,志愿服务是我国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着力点,能否通过志愿活动的普及让志愿精神走向常态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渠道。传统的仁爱元素转化为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价值,经由志愿服务的平台呈现为邻里守望互助、关心困难群体、热心公益事业等各个层面。其次,志愿服务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通过志愿服务的制度化、专业化来满足公众日益多元的需求,是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所要求的。最后,志愿服务是促进社会健康转型的关键纽带,在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通过志愿服务促进不同阶层、不同代际、不同地域的群体有机整合、形成共识,是塑造社会信任的重要机制。
在发展中,我国的志愿服务越发成熟,不同程度地肩负起了三项重任。但整体上而言,各类志愿服务工作仍在不断地遭遇各种困境。这种“失灵”的情况有些是时段性的,有些则是结构性的。具体而言,在本土创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过程中,我国志愿服务组织仍在寻找灵活且高效的工作机制,以求适应各地、各领域的需求。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作为治理技术的志愿服务如何进行顶层设计、如何形成具体的制度、采用怎样的策略落地等都在调整中,所以出现“失灵”是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是所谓的时段性“失灵”。但与此同时,我国志愿服务的三项重任,即参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参与社会治理和促进社会健康转型,对志愿服务发展方向的引导和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这就导致了志愿服务的结构性“失灵”。
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期望以志愿服务为平台,传播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理念,注重在志愿服务中培育社会成员利他的、和睦的、团结的、积极的精神。所以,志愿服务的普及化很重要,如此才能让社会成员在共同的经历中、在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对彼此的关怀和对整个社会的关切。并且,志愿服务的动员策略、激励机制、组织制度等都应当以精神培育为目标,注重长期的影响和效果。
而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志愿服务应当从自身的知识体系出发,动员社会成员参与治理,既为社会成员提供表达诉求的平台,也促使社会成员力所能及地以非营利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在这样的目标下,志愿服务应当追求专业化的发展,从而提升志愿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并且,志愿服务应当关注个体当下的需求,并以此为依据追求多元的组织形态、覆盖更多的领域、采取多样的激励方式,从而更广泛地激发参与、满足需求。
志愿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在社区、单位等各个生活和生产的组织中提供了交流情感、建立认同、协同行动的平台,为社会整合提供了有效的机制,进而得以促进社会的健康转型。因而,若以促进社会健康转型为目标,志愿服务应当重点关注行动和组织过程中如何化解矛盾、培育信任,继而塑造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基层防范社会风险、解决社会问题。
这三项重任内在上本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精神文明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形成、社会顺利健康转型的基础。社会治理形成的良性的运转机制则会进一步促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并且可以防范和抑制社会矛盾,有益于社会健康转型。而不同阶层、不同代际、不同地域的社会成员得以整合,既反映了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又与社会治理的目标一脉相承。但是由于三项重任在短期和长期所强调的目标和价值存在张力,对志愿服务在理念层面和实践层面上的要求和期待就有所不同。
在理念层面上,三项重任对志愿服务价值中利他与利己、义务和自愿的偏好取向是不同的。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是多样的,或基于利他动机,或基于利己动机,或两种兼有,或动机模糊,而志愿服务在结果上既是利他也是利己的——对于志愿者和服务对象都有益。于参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而言,其内核强调志愿服务的利他性,由此弘扬奉献、乐于助人和团结友爱的精神;于参与社会治理而言,其关注个体的需求,更倾向于通过志愿服务中利己的一面来调动资源、吸引社会成员的参与;于促进社会健康转型而言,其并不强调志愿服务的利他性或利己性,而强调社会成员对两者的兼容,尤其是尊重和接纳他人和自己对两者的认同差异。此外,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志愿服务的发展既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也从国家层面强调动员和号召的义务性质。于参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而言,其强调志愿服务参与者发于本心的自愿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向循环的精神培育机制;于参与社会治理而言,其从制度上强调对志愿服务的义务性塑造,从而保障社会治理的动员和激励效率,让志愿组织具有稳定而充足的人力资本;于促进社会健康转型而言,其兼容志愿服务的自愿性和义务性,但强调基于两者的制度设计在面向社会成员时是公平的。
在实践层面上,三项重任对专业化还是普及化、物质提供还是精神培育、制度化还是常态化的强调程度也是不同的。首先,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尤其强调志愿服务要普及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规模和范围更广的社会成员中培育和塑造精神;社会治理强调形成可持续的服务供需机制,这要求志愿服务走向专业化;促进社会健康转型的目标要求兼顾专业化和普及化,但在专业化和普及化的进程中,要通过与社会成员的充分沟通,让不同的理解、价值和方法在人们的交流中得以碰撞。其次,尽管志愿服务既有物质资源的流动,也有精神的培育和交流,但显然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更重精神,而社会治理更重实质的服务,社会健康转型则要求资源的带入和精神的激发都要避免激发矛盾。最后,制度化和常态化是志愿服务发展所必须实现的: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更重常态化,试图让志愿服务化为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习惯;社会治理更重制度化,期望让志愿服务建立完整的组织机制从而保障服务的延续和治理格局的稳定;社会健康转型则要求对两者的同步追求,以期社会成员能够在稳定的机制下将志愿服务变为生活的一部分。
可见,这三项重任不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对志愿服务发展的首要目标有着不同的强调。这使得在我国,志愿服务体现的“失灵”不仅是与“奏效”相伴的时段性结果,也是基于三项重任而必然经历的结构性结果。但这种结构性不是出于志愿部门与其他部门在理念体系上的分异,而是出于其多重的、具有内在张力的任务导向。所以,中国语境下的志愿服务“失灵”是异常复杂的,因为志愿服务的发展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影响,肩负了多重任务,需要同时解决很多急迫的问题:其在既有社会基础的影响下吸纳了来自其他文化的思想;其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力求建立可持续的、稳定的、能够正向循环的机制;其作为一项治理技术嵌入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既要在国家的引导下开展工作,又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其还要在兼顾利他和利己、义务与自愿中,注重专业化和普及化的共同发展,协调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收获,实现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所以,急需寻找契合我国本土特色的理论工具和恰当的剖析角度,来探索让志愿服务发挥成效、走出“失灵”的道路。
本书正是带着这样的旨趣,关注了青年支教这样一个特殊的志愿服务领域。一方面,选择支教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出于笔者在资料获得上的便利性;另一方面,支教实质上是一种教育和公益的结合形态,而这种结合形态本就是学者们在我国语境下研究福利事业时常用到的分析对象。像梁其姿就以义学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我国明清、近代社会中福利实践的变迁,进而探讨我国社会的机理。她认为,教育和施善是时代激变中社会各方融合新旧价值、应对新的社会问题等谋求稳定的主要着力点,而且两者往往并肩而行。和传统的义学一样,支教在社会的转型中既发挥了传播社会价值观的作用,也有更切合实际的功能,即让社会成员获得学业或职业技能上的支持。这显示出支教所承载的参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健康转型的重任,与义学在明清、近代所承担的功能有相通之处。这就使得,本书虽不是历史研究著作,也并非要解读当代支教在发展中的来龙去脉,但与以往的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在讨论上也就能够有所比对和延展。因而,本书在回顾以往中西研究的基础上,以青年支教为分析对象,在我国的语境下对志愿服务展开分析。
©️本文版权归作者【先晓书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分享
- 评论(0)
- 点赞(0)
- 收藏(0)